徐英瑾评《人工智能简史》︱人工智能,真的能让哲学走开吗?

最近尼克先生写了一本新书,题目叫《人工智能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12月)。因为我本人最近十来年一直从事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自然就在第一时间买来一本阅读。在这篇书评里,我想特别谈谈该书的第九章。该书的第九章《哲学家和人工智能》主要就是为了挤对哲学家而写的,特别是为了挤对那些对人工智能有话要说的哲学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国内大多数理工研究者对哲学的某种深刻的偏见,即:咱们的地盘,哲学家少插嘴。
对哲学家是否有资格对科学问题插嘴,作为科学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双料研究者,笔者觉得自己的确有话要说。我承认:并非面对所有理工科问题,哲学家都有话要说。譬如,关于“歼-20为何用鸭式布局的形体”这个问题,哲学家就不会发言,至少不会以哲学家的身份发言。但关于“进化论是否能够沿用到心理学领域”“量子力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些科学家都未必有定见的问题,心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与物理学哲学当然有话要说。很多人会问:你一个学哲学的,有什么资格对这些问题说三道四?答案很简单,在海外,处理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往往有两个以上学位,比如神经哲学的专家丘其兰夫妇(Paul Churchland, Patricia Churchland)都有很深的神经科学背景。你即使看到某个只有哲学学位的中国学者对某个科学问题的发言有失水准,也不能推断出这个行当整体上不行,因为事情的真相可能仅仅是:这个行当的高手不在你的朋友圈里。
按照同样的逻辑,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哲学家当然可以发言。道理很简单:符号AI与联接主义AI关于何为智能的基本定义都不清楚,可见关于人工智能该怎么做,业内并没有统一意见,就此多听听哲学家的见解,恐怕也没有啥坏处。有人会问:问题是哲学家连一行程序都不会写,为何要听哲学家的?对这个疑问,两个回应足以将其驳倒。

第一,你怎么知道哲学家都不会写程序?比如,知识论研究里的一位重磅学者波洛克(John L. Pollock)就曾开发了一个叫作“奥斯卡”的推理系统,相关研究成果在主流人工智能杂志上都发表过。再比如,今天在英美哲学界名声赫赫的心灵哲学家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是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大AI专家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的高足,以前也和老师一起发过AI论文,难道他竟然不会写程序?
第二,难道一定会写程序才是能够对AI发表意见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底层操作,写具体的代码的工作,类似于军队中最简单的射击动作。然而,大家请试想一下: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究竟是因为他有运筹帷幄的本事呢,还是因为他精通射击?答案无疑是前者。很显然,哲学之于人工智能的底层操作,就类似于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之于射击之类的战术动作。

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尼克先生显然没有给予哲学家以我这般的高度重视。他在该书第九章列举了三个与人工智能有交集的哲学家,一个一个予以批判。第一个是德瑞福斯(Hubert Dreyfus),即试图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批判符号AI的现象学家。第二个是塞尔(John Searle),即试图通过“中文屋”论证,来反驳强AI的可能性的语言哲学家。第三个则是普特南(Hilary Putnam),即试图通过“钵中之脑”思想实验,来证明语义外在论之正确性的分析实用主义者。然而,从论证角度看,尼克的相关讨论显然会有“不完全归纳”的风险:就这么三位哲学家,能够代表哲学界对人工智能的一般看法吗?譬如,前面提到的查尔莫斯与波洛克,作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就拿作者所提到的塞尔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来说,他也好像完全忽略了一个与该论证相关的基本事实: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的至少几百篇评论塞尔该思想实验的英文哲学论文,大多数都是批评塞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拿塞尔的观点做哲学家的典型,是不是有点偏颇呢?

除了归纳不完全的问题之外,尼克先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真的理解他所批评的哲学家的工作吗?就拿普特南来说,他其实是个很不错的数学家。他对层次分析法的研究,在一般计算理论的文献里都会被提到,而计算机文献里提到的“戴维斯-普特南算法”(Davis-Putnam algorithm),其中也凝结了普特南的心血(后来这个算法又演化为了 DPLL 算法)。诚然,晚年的普特南对人工智能是流露出了一些敌意,但是他早年对“多重可实现性”概念的研究,实际上为强人工智能论题的话语框架提供了基本表述手段。而在尼克的描述中,普特南作为人工智能同道人的这一面基本被抹杀了,留下的则是一个愚蠢的、漫画式的科学外行形象。

而更多的误解则出现在作者对德瑞福斯思想的描述中。作者似乎对德式哲学的真正思想背景——海德格尔哲学——很不屑,认为这种哲学毫无算法性说明支撑,纯粹是卖大力丸与狗皮膏药的人在瞎吆喝。老实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地反对尼克对海氏哲学的批评。作为英美分析哲学研究者,笔者有时候也对海氏的表述方式感到抓狂。但与尼克先生不同的是,我并不怀疑海氏哲学至少说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尽管关于如何将这些洞见说得更清楚明白,我与“海学圈”主流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笔者的正面观点是:只要能够将海氏哲学思想“翻译”得清楚一点,他的洞见就更容易被经验科学领域内的工作者所吸收。
——那么,怎么来做这种“翻译”呢?非常大略地说,海氏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关心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而他自己的新哲学要重新揭露这被遗忘的“存在”。我承认这是海的“哲学黑话”,不经解释的确不知所云。但它们并非在原则上不可被说清楚。现在我就尝试用通常的汉语进行解释。
所谓“存在者”,就是能够在语言表征中被清楚地对象化的东西。比如,命题、真值、主体、客体,都是这样的存在者。而“存在”本身,则难以在语言表征中被对象化,比如你在使用一个隐喻的时候所依赖的某种模糊的背景知识。你能够像列举你的十根手指一样,将开某个玩笑时的背景知识都说清楚吗?在背景知识与非背景知识之间,你能够找到清楚的界限吗?而传统AI的麻烦就在这里。人类真实的智能活动都会依赖这些说不清楚的背景知识,而程序员呢,他们不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就编写不了程序。这就构成了人类的现象学体验与机器编写的机械论预设之间的巨大张力。
有人会说:机器何必要理睬人的现象学体验?人工智能又不是克隆人,完全可以不理睬人是怎么感知世界的啊?对这个非常肤浅的质疑,如下应答就足够了:我们干嘛要做人工智能?不就是为了给人类增加帮手吗?假设你需要造一个搬运机器人,帮助你搬家,那么,你难道不希望他能够听懂你的命令吗?——譬如如下命令:“哎,机器人阿杰啊,你把那个东西搬到这里来,再去那边把另外一个东西也拿过来。”——很显然,这个命令里包含了大量的方位代词,其具体含义必须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不指望机器人与你分享着同样的语境意识呢?你怎么能够忍受你的机器人是处在另外一个时-空尺度里的怪物呢?既然这样的机器人必须具有与人类似的语境意识,由海氏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现象学体验的某些基本结构,难道一定意义上不也正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体吗?

有人还会说:那么,我们又该怎样找到一个算法化的结构,来落实海氏哲学的上述洞见呢?比如,如何在算法的层面上刻画“存在的可能性结构”呢?你给不出算法化的结构,不等于白说吗?但请读者想清楚了,这个要求应当是提给人工智能的,而不是提给哲学家的。或者换一个说法:海氏哲学的见解,可以说是浓缩了人类用户对人工智能的“用户期望”,而实现这些期望的负担,本就应当放在人工智能工作者的肩上。这就好比说,如果军方要求飞机研制单位制造一种隐性战斗机的话,那么,如何设计这种飞机的任务,本就应由研制单位来负责,而不是由军方来负责。换个说法:你不能反过来指责因为用户不懂技术的细节而没有资格提出“用户要求”,就像你不能因为军方代表不懂飞机设计的某些细节问题,而去指责其没有资格去撰写军用航空器的设计标书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真像尼克先生那样,仅仅因为海德格尔主义者暂时没有算法表述支持,就将其一棍子打翻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凭借同样的理由去解散全世界的消费者维权组织了——消费者懂什么技术细节啊。而也正因为这一“归谬法”推理的结论是荒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反推出:尼克先生是将本该放在人工智能研究者肩上的责任放到了哲学家身上,由此转嫁了责任,并冤枉了好人。

德瑞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人工智能哲学家即使在主观上不想去理睬哲学,但是客观上总是会不自觉地预设某种哲学立场——而且,也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哲学鉴赏力,其不自觉采纳的哲学立场往往还很低端。譬如,明斯基的框架研究的基本思想,就是胡塞尔早就玩剩下的东西,并且早就被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批判过了。不过,对此评论,尼克先生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哲学家都是自恋狂,以为别人的思想都是源自于自己的。也就是说,明斯基的想法完全可以独立于胡塞尔的框架,在这个语境中提出胡塞尔的大名完全是没必要的。
而在笔者看来,尼克先生在这里又陷入了对哲学家见解的严重误读。德瑞福斯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明斯基正是因为读过胡塞尔,才有了他的关于框架的设计。他的意思毋宁是说:某种错误的思想在西方思想界普遍流传,以至于哲学家与工程师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尽管工程师本身未必知道哲学家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也正因为哲学家对类似错误思想的表达更为凝练、更为系统,所以在哲学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才能够把问题说透。

当然,我本人对德瑞福斯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他更激进。我赞成他对所谓符号AI的批评,但是他对神经元网络技术的温情,我是不能接受的。毋宁说,神经元网络是无法灵活地在不同问题领域之间切换的(譬如,会下围棋的系统不能直接用来处理股票),也不能有效地应对句法生产的灵活性与创生性(因为纯粹的统计是无法预报新的意义组合方式的)——在这个问题上认知科学家派立辛( Zenon Pylyshyn )与刚刚离世的哲学家福多(Jerry Fodor)早在1988年就撰文批评过了(福多这么有名的认知科学哲学家,尼克先生全书也几乎未提一字)。换言之,我本人即使认可“海德格尔式的AI”这个提法在字面上的可行性,我对这一标杆的高度的估计,也比德瑞福斯更悲观。

抛开尼克先生对德瑞福斯的误解不谈,他对一些别的重磅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的误解也是惊人的。譬如,他认为维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的“积木世界”的思路是接近后期维氏语言哲学的。这其实是让任何一个对分析哲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要失笑的结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圈”是奥斯丁与斯特劳斯的日常语言学派成员,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干干净净的句法分析,拉回到充满混沌与沼泽的日常语用的地面,并对任何公理化的思路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疏离感。考虑到“积木世界”的程序设计背后鲜明的公理化色彩,将这一进路看成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类似物,恐怕才相对更为可靠。由此看来,虽然作者未必不熟悉维特根斯坦生平中的某些八卦,但他肯定没有读懂《哲学研究》,而且,也肯定没有读过笔者本人的著作《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说了那么多尼克先生对哲学的误解,笔者还想谈谈他对认知科学的忽视,以免让人觉得笔者过于“哲学本位主义”。实际上,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后不久,认知科学也在西方诞生,1956年实为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的“双生年”。但纵观全书,尼克先生似乎对认知科学方面的事情提得非常少。譬如,人工智能的元老司马贺(H.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研究,实际上就具有横跨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三重意义,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成为图灵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双料得主了。但对于司马贺这方面的工作,作者似乎也显得漠不关心(经济学家注意了!尼克先生除了鄙视我们哲学家以外,也瞧不上你们)。好在笔者本人并不是像尼克拒斥哲学那样去拒斥认知科学与经济学。希望了解类似思想背景的读者,建议读一下笔者写的相关科普小书《认知成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而且,也正因为尼克先生缺乏对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科学之间关联的讨论,他整部著作的结构框架显得非常散乱。他对机器定理证明的高度重视,抢夺了他讨论一些别的重要话题的篇幅,比如贝叶斯网络(贝叶斯网络的发明人、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的工作也被忽视)。而他对神经元网络技术的讨论,亦忽略了深度学习技术最近在该方向上的发展(譬如,他仅仅在讨论“阿尔法狗”时略提了一些相关技术,但却没有很好地介绍深度学习大牛Geoffrey Hinton的工作)。至于他对计算理论的基础知识——图灵机的介绍,竟然被放到了第十章,这就好比一个教日语的老师在第一课就教学生日语中最难的敬语,然后要等到第十课再教最基础的五十音。当然,这部书也是有独到贡献的。比如,全书第四章在介绍日本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时所披露的一些细节,在一般中文读物中是读不到的。要是该书余下各章都这么言之有理,该有多好啊!
最后笔者还想做出两点引申性评论。第一,哲学当然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尽管事实上有能力切入人工智能话题的哲学家的确不多。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首先是一个规范性命题,而不是事实性命题,而后者是推不出前者的——譬如,你从“清末的中国很少有外文人才”这一点出发,是推不出“清末的中国是不需要外文人才的”。同样的道理,作者用维基百科的文献统计系统得出的“现有的哲学文献与人工智能文献关系不大”这一观察,也推不出“人工智能本就不需要哲学家来插嘴”这一结论。
第二,广大读者若真想比较系统地了解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互动的大历史的话,还是得读一下认知科学哲学家写的读物,因为认知科学哲学家的训练是横跨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比较容易免受狭隘的学术偏见的影响。而就这方面的读物而言,笔者除了想再厚着脸皮再推荐一下拙著《心智、语言和机器》之外,还想推荐英国资深认知科学哲学家博登(Margaret Boden)的名著《作为机器的心灵——认知科学史》,这亦是必读的(可惜该书尚无汉语版,顺便说一句,此书作者有计算机、医学与哲学多学科背景,与诸多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大牛有私交,是大咖中的大咖)。读者如果能够将博登老太太的书与尼克的书相互比照阅读的话,恐怕就马上能够看到“歼20”与“歼7”之间的那种品质区别了。不过,尼克先生的著作并没有提到博登的这部厚达一千六百三十一页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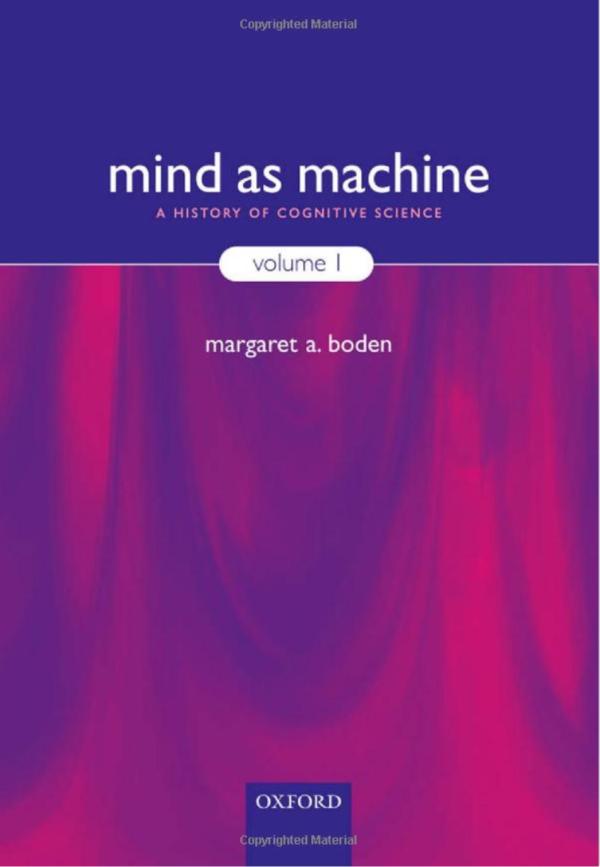
笔者承认,笔者的这种“让哲学介入人工智能”的观点,并不是当下中国舆论圈的主流声音。关于AI这个话题,中国主流舆论圈的声音背后恐怕都有资本力量的推动,而在资本界对利益回流的热切期望与哲学家反复推敲的“迟缓”工作作风之间,一直是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的。不过,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特别觉得哲学家更有必要发出声音。一切逆风而行者的坚定,均来自对风向转变的信心。笔者恰恰不缺这点信心。
(本文作者为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人工智能哲学”分会场中方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