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前沿论坛:走出“唐宋变革论”,迈向“大宋史”研究
2017年10月21—22日,“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西部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承办。上海师大古籍所教授、宋代法制史专家戴建国是本次会议召集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四十位学者与会,其中不乏著名的宋史学者,比如老一辈的朱瑞熙先生、龚延明先生,史金波先生、汪圣铎先生也提交了论文(因故未到会),还有相当引人瞩目的包伟民、李华瑞、葛金芳、程民生、陈峰、程妮娜、虞云国教授等学界大腕。因大多数与会者都是教授(或研究员),为行文简便,下文一律不加“教授”等头衔,敬请明鉴。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论坛是“大宋史”专家学者聚在一起切磋、交流的会议。所谓“大宋史”,是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1982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旨在强调当时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这个理念对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次论坛可以看作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大宋史”学界同仁的对话与交流。论坛上的报告和讨论相当精彩,甚至不乏激烈的交锋,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无法就每一位专家的报告展开报道,大体上按讨论比较集中的主题稍作归纳整理,挂一漏万,请诸位专家与读者谅解。

学术回顾:从“积贫积弱”论到“宋粉”成群
简单的会议开幕式过后,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先后作主题报告,题目分别为《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宋史辞典>前言》。包伟民在报告中指出,“40年来辽宋夏金史领域的学术推进尤其明显,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国人对公元10至13世纪——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产生了近乎逆转性的变化”。一个外在的表现是,以前一提起宋朝,人们往往联想到“积贫积弱”这个定性的判断,而在当下,中青年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中国史内部来认识宋代的发展,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予新的评价”(李华瑞语);同时,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宋粉”,极力推崇宋代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他也指出,近一二十年“大宋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激增,学术大跃进的态势十分明晰。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进步带来的更多却是临深履薄之感”,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普遍产生了一种焦虑心态,其具体表征有:研究方法的缺失感,由此形成“理论饥渴症”;对时代定位的困惑,“唐宋变革”说的大行其道就是这种困惑的一种反映。
朱瑞熙是《宋史辞典》的主编,他主要介绍了这部辞典编纂的经过,尤其是在“两位专家撰写好的共一万五千多词条全部失踪”的情况下,“再请四位教授重起炉灶,分头编纂”,“广泛吸取学术界特别是宋史研究同仁研究成果”,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为推动宋史研究提供便利。

“大宋史”研究如何可能?
邓广铭在将近四十年前就提出“大宋史”的概念,在辽、宋、夏、金学界内部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也出现了不少致力于“大宋史”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概念似尚未超出“大宋史”研究领域,影响力还比较有限,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陈江所注意到的,百度百科收入了众多与会学者的人名条目,却没有“大宋史”这一词条。而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就是邀请到研究辽、西夏、金的专家与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关志国合作的《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史学》(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王晓龙代读),对传世文献中的民族史撰述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包括宋代官修正史、宋代会要、使臣见闻录与笔记、南方民族史专著、大型类书、地理总志等,特别提及少数民族文字记录的民族史撰述,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回鹘文、藏文、傣文等。
吉林大学程妮娜专攻辽金史,她的报告《辽宋金内在联系的探索》,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考察政权基本制度与文化的历史继承与彼此的影响,二是讨论大一统政治观念的继承与正统之争,三是辨析汉人在辽宋金发展中的作用。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彭向前在论文中呼吁开展西夏与宋辽金史比较研究,促进西夏学与藏学之间的合作,并举例说明跨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他研究指出,以往学界常常误把一些文献中的“大食”当作阿拉伯帝国,认为西夏与阿拉伯帝国有贸易往来,其实那个“大食”是指喀喇汗王朝。
华东师大陈江的《“大宋史”与“新清史”》以近年引起热烈讨论和争议的“新清史”为镜鉴,提倡“整体性”研究,期望走出“汉化”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模式。
包伟民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所谓“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同时做宋史、西夏史、辽金史,而是指在从事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研究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

“唐宋变革论”可以休矣?
论坛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近些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唐宋变革论。有意思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和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文提交的论作都与唐宋变革论直接相关,可见这个话题的“火热”程度。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础讨论宋代问题”,将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滥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面对这种现象和态势,李华瑞先肯定了唐宋变革论对推动国际宋史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接着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继续炒冷饭、吃别人剩下的旧馍,无助于推动研究的进步,反而“弊大于利”。然后他从学术史、政治、性别、多民族国家、国际宋史研究和“问题意识”等方面,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由此,他认为宋代近世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叶”。
另外,李华瑞还强调了六点:一是历史分期问题目前在中国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都不再是热点问题;二是“宋代近世说”的实质是中国文明停滞论,背后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三是这一假说立足于“中国本土”,历史空间逐步缩小,相反,应多提倡和回应“大宋史”的研究理念;四是“宋代近世说”虽然讨论很热烈,但真正与它对话的著作很少,对唐宋史研究的实际推进收效甚微;五是学术研究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断推陈出新;六是借此反思“我们自身的研究”,站在现今的角度观察和把握历史。
其中第三点特别值得重视。张文在评议中指出,“唐宋变革论”只考虑了内部的纵向变迁,没有考虑同时代横向的地理空间上的影响。
与李华瑞和“唐宋变革论”说“拜拜”的态度不同,张文更倾向于对这一概念做一些调整,“使这一问题重新回归本土解释框架”。在他看来,唐宋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唐以前,大体可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体化阶段,中唐(以两税法实施为界)以后,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至北宋,形成国家—社会两分化模式。他认为,宋代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性质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体制分化导致经济繁荣、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国家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总之,他认为唐宋时期确实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但这项变革不是技术层面的革命推动的,而是由体制分化造成的。
李华瑞在评议中重申,他说唐宋史研究应该走出“唐宋变革论”,是指内藤湖南提出的那个假说,从学术规范、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内藤的假说是有特定内涵的,包括贵族政治、平民社会、文艺复兴说等,如果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发现其中的变革,那应该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这样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利于学术进步。他同时澄清,并不是说不要研究唐宋时期的变化,相反还要继续探讨中国历史长时段中的分水岭,至于怎么定性、怎么研究,概念一定要明晰。

对于这样针锋相对的学术意见,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直言:学术研究就是要提倡“分裂”,不能搞思想统一,你说东我就一定要说西,这样才有利于打开思路,促进问题的探讨。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吴铮强报告的题目是《宋史还能谈什么?》,他本来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但限于时间,只讨论了“唐宋变革论”问题。他也认为不必再讲唐宋变革论,但他的理由与李华瑞的不同。李华瑞从各个角度探讨唐宋变革论的实质,发现很多方面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告别唐宋变革说。而吴铮强认为,“宋代近世说”本来就是社会进化论在历史学上的运用,如果还是带着社会进化论的视角观察历史,即使否定了“唐宋变革”,也会出现新的“变革说”,比如两宋变革、宋元变革,等等。吴铮强还指出,有学者认为郑樵、陈邦瞻等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唐宋之际的变革,但这些人并不是从“宋代近世说”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作为传统士大夫,是站在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认识典章制度的变迁的。如果我们不考虑治国平天下的问题,陈邦瞻他们那套唐宋变革说自然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戴建国在综合讨论环节指出,“唐宋变革论”所说的变革是从唐中叶到五代的变革,而名字又叫“唐宋变革”,是不是应该包括宋代的变革?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待厘清。

史料的扩充:应重视非文献材料的价值
一般而言,视野的扩张必然要求扩充史料,史料的扩充必将造成视角的转换。宋史研究的史料扩充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在《宋史研究中的两个较大问题》中呼吁,要更加重视研究“宋代原始遗物”。华东师大陈江认为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献的利用,要加强对考古发掘资料的利用和重新解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虞云国则尝试利用图像史料,倡导宋史研究与宋元美术研究之间的互动。他还在报告中“自我检讨”:以前写宋宁宗时,将他定为弱智。后来他看到龙美术馆的一个特展,从美术史料中发现宁宗的题画诗,“若不能证明其出自他人代作,则其诗才尚可,原来的结论就要质疑”。中山大学曹家齐则以古琴曲《潇湘水云》为例,探讨宋元音乐史的问题,以期实现艺术史与宋史研究的互动。
上海师大古籍所戴建国也对拓展史料来源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倡议借鉴元明清学界的成果和资料,深挖宋代相关文献价值。他还以朱瑞熙先生《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为例,指出该文是作者拜读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后,关注明代的粮长、元代的社长和主首与宋代乡村催税人的关系,最后得出“明朝的粮长制还是脱胎于南宋的税章和苗长制”的结论。另外,戴建国还强调要重视开拓新的史料源,与唐史学者相比,除了个别学者,大多数宋史专家对墓志的利用和研究还不够充分。此外,元明清三朝文献中散落的宋代史料也很值得挖掘。这些都体现出宋史研究“往后看”的视野。

包伟民在综合讨论环节指出,“对于非文献材料的敏感度,我们可能不如唐以前那些断代的学者,主要的原因是宋史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既然文献材料都够‘受罪’了……而唐史学者因文献材料所限,对边边角角的材料都要尽力去挖。”包伟民还主动自我反省,说他推荐图书馆购买《宋画全集》,但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去看。由此引申开来,就需要研究者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得老老实实去学”。
数据库与“大宋史”研究
新技术手段对历史学界会带来什么帮助,会造成哪些冲击?近些年,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GIS(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库的信息在微信朋友圈转得热火朝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对数据的“饥渴”与兴奋。本次论坛有两位学者涉及这一话题。
一位是浙江大学龚延明先生,他主要介绍了自己的检索型数据库——以《宋代登科总录》为数据来源,可按照字号、籍贯、职官、谥号等关键词检索相关信息,借此了解宋代科举家族的形成、宋代进士地域分布的差异以及宋代科举制度东传与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等问题。但这一数据库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还无法上线,供学人公开使用。另一位是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耿元骊,他以CBDB为例介绍了关系型数据库的运用和学术意义。他在报告中指出,“从学术突破来看,利用CBDB而取得较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还很少,或者说没有,只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得以呈现。如何利用这样的关系型数据,出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可能很重要,这对于关系型数据库能否继续生存有很大意义。”
包伟民在综合讨论环节指出,面对新技术,不能采取抗拒的态度,而应该给予正面的回应。在电脑检索的时候,只能字对字,查到“张三”,它就以为是“张三”了,但文献实际讲述的意思是个隐喻呢,这样一来,电脑就无从判断了,技术人员也不太可能了解这种情况。再比如,A和B的交往有50次,A和C的交往有20次,根据这个检索结果,就能判断A和B的关系比A和C的关系更加密切吗?天晓得!说不定记载较少的,关系反而更密切呢。还有,史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叙述,再将这种叙述置换成数据,如果用这种数据来检索,对文献本意的曲解可能会更加厉害。比如,元末明初,士人是否做官“失节”,如果把没当官的算作“正”,当官的算作“负”,看似很有道理,可是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有的人想当而没当上,有的人迫于生计而当官呢,这种数据化就很容易造成误导。通过这几个例子,包伟民说明大数据对历史研究只是一个辅助,不能产生依赖心理,不必对大数据过于兴奋。历史研究最核心的还是如何发现材料,如何体会历史文本的问题。

总体而言,这次论坛偏向宏观思考的多,微观研究的较少,不过也有一些报告值得关注,比如上海师大古籍所汤勤福的《金朝“五礼”制度抉微》、中山大学历史系易素梅的《宋代奸的罪与非罪》、华东师大古籍所刘成国的《新见宋人墓志与王安石的日常行实考述》等。上海师大古籍所几位青年学者的论文也可圈可点,如孔妮妮《晚宋理学家的学术视界与君臣理想——以<大学衍义>为中心的探索》、韩冠群《御殿听政:南宋前期中枢日常政务的重建与运作》、雷家圣《高遵裕与宋夏灵州之役的再探讨》。
另外,北京师范大学葛金芳的报告《在共识性结构中重新定位宋代社会》重申他的“农商社会”说,引起包伟民的质疑;他的“宋代道统高于政统”论,也遭到包伟民的反对,并引起李华瑞、汤勤福等学者参与讨论,形成论坛第一个交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陈峰的《宋朝分权制衡的治军特点与边防困境》认为,宋朝在治军上实行的制衡原则,贯穿于兵权运作的各个重要环节,给边防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上海师大雷家圣对此提出几处疑问。格于本文体例,为免枝蔓,恕不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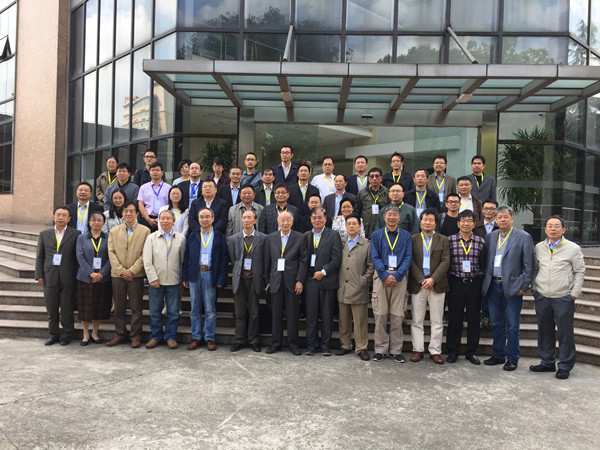
包伟民在总结中表示,这次论坛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讨论的核心议题,有的初步形成了共识,有的则需要尝试和探索各种应对的方式,让人感到意犹未尽。比如吴铮强提出的“宋史还能谈什么”,虽然没有讨论起来,但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萦怀于心。至于如何推动学术进步,在包伟民看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旧题新作,还是要关注和重新验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核心议题,不能假定既有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另一条就是走向历史细节,“向前看”、“往后看”,注意宋朝与其他政权的角逐,在更大的格局和视野下讨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