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美国》:历史学家如何看待美国的枪文化和枪支管制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日晚,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枪击案。这是美国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大的枪击案,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究”对此事件十分关注,并选取相关文章发布,一方面,用以寄托对这场“大屠杀”中丧生的人们的无尽哀思,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希望从历史的维度,激发读者对美国相关历史的思考。本文原题《历史学家的责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载《学术界》2002年第5期。作者任东来,生前为南京大学教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2001年4月18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美国关心枪支管制的人和历史学家来说,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日子。这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把美国历史学界最负盛名的著作奖——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颁给了美国艾默利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贝勒斯雷斯(Michael A. Bellesiles)的大作:《武装美国:全民枪文化的起源》(Arming America: The Origins of a National Gun Culture)。但就在颁奖仪式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保守派人士召开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讨论会,请几位历史学家专门批评该书。更妙的是,美国专门播放公共政治事务的电视台C—Span2在第二天(星期天)晚上的黄金时间,专门报道了颁奖和批评会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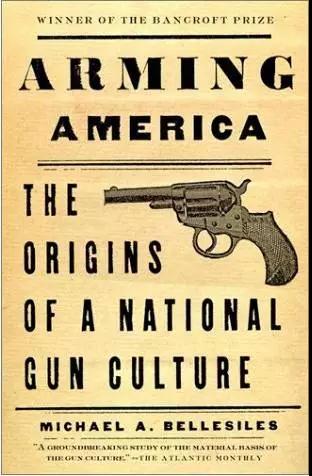
虽然班克罗夫特奖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地位,获奖者也可以立马成为学术界的超级明星。但历史学毕竟不是“显学”,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奖的社会影响根本无法和普立策奖或全美图书奖相提并论。那么,此书何以会引起美国媒体和一些利益集团的如此注意?这话还要从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说起。
美国独特的枪文化
我们知道,美国独特的枪文化令美国人头痛不已。接二连三的校园枪击案,推动了美国社会要求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之一——全国来福枪协会(NRA,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通过游说保守的共和党议员,竭力阻止国会通过任何妨碍他们利益的立法。结果,枪支管制和妇女堕胎等社会问题一样,居然成为冷战后美国一个全国上下关注的政治问题,两派经常为此吵得不可开交。保守派认为这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开明派(liberals)认为,它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问题,是美国凶杀案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来福枪协会之所以有恃无恐,最主要的是由于《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这个尚方宝剑撑腰,该条规定:“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一个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须,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但反对者认为,这只是指民兵可以拥有武器,并不是说每个个人也可以拥有。但这一解释不占主流,持枪权200多年了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人基本的宪法权利。
一书激起千层浪
要弄清楚持枪权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它的历史渊源,而这恰恰是美国学术界研究不够的题目。于是,贝勒斯雷斯博士抓住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题材”,紧扣时代主题,出版大作《武装美国:全民枪文化的起源》,考察了从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到1877年为止美国枪文化的发展。他的基本看法是,枪文化并不是美国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固有的部分,它实际上是对由联邦政府监督下不断增长的武器生产的反映。特别是由于美国内战,社会对武器的需求有了急剧的增长,枪支数量越来越多。这一结论挑战了美国成年男子都拥有武器的神话,特别是在殖民时代,美国人很少拥有可以使用的枪支。因此,美国的枪文化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传统”(an invented tradition)。
在出书之前,1996年他就以此为题在美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杂志《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发表论文,并获得美国历史学者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OAH,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协会)本年度最佳论文奖(Best Article of the Year)。大作出版后, 更是好评如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发表了专家赞扬性书评, 强调作者所用的遗嘱资料说服力强,“绝对新颖,引人入胜”。连耶鲁大学教授、美国殖民地史研究泰斗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都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发文赞扬该书“资料无与伦比,尤以遗嘱记录为最佳”。由于这一题目的现实社会意义,更是由于这一结论支持了自由派严格枪支管制的主张,于是,受到了有关利益团体异乎寻常的关注。

一些法律学者说,这一观点可能会影响联邦法院对最近几件挑战枪支管制法律的判决;枪支管制倡导者更是兴高采烈,对美国的枪文化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传统”观点大为赞赏,主张枪支管制的主要利益集团之一—— 阻止手枪暴力中心(Center to Prevent Handgun Violence)和美国律师协会(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2000年2月,专门召开讨论会,请贝勒斯雷斯和其他著名历史学家共同讨论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真正含义。
由于溢美之词主要来自开明派学者,不免使保守派怀疑这种赞扬是否是因为它确认了前者长期以来坚持的一种信念: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只保护集体的持枪权,而个人的持枪权在宪法起草和批准过程中并不重要。这一怀疑不无道理,因为贝勒斯雷斯得出的结论,的确是石破惊天。反对枪支管制的人认为贝勒斯雷斯的研究是个阴谋,想证明如果殖民地时代只有极少人拥有枪支的话,那么,宪法的制定者可能无意把“持枪权”应用到个人。
俗话说,树大招风。引起学界和社会如此反响的著作自然会引来一些“好事者”挑剔的审查,更何况此书涉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一些怀疑贝勒斯雷斯研究结论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花了一年的时间,亲自核对了他所利用的一些资料,发现贝勒斯雷斯不仅非常严重地滥用史料,而且有编造之嫌。他们表示,如果全面彻底地核查的话,作者的这项研究可能是近年来美国人文学术界最恶劣的丑闻。
但贝勒斯雷斯坚决否认他有意误用史料。他反驳说,对他的批评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的动机。
批评家穷追猛打
毫无疑问,如果贝勒斯雷斯的著作不是涉及到枪支管制这样敏感的政治问题, 如果不是受到广泛赞扬从而引起普遍注意的话,大概是不会引发其他学者对其著作进行严格审核的。指出其著作存在严重问题的学者既有出于政治动机的保守派人士,也有主张枪支管制的开明派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受有关利益集团的指使。他们之所以产生怀疑,是源于贝勒斯雷斯自己的说法。他声称,他一共读了1.117万份死后财产清单(遗嘱清单,probate inventories),这些文件分散在全美40个县中。他发现在1765-1791年间,只有14%的财产清单中列有枪支,而且这“其中一半以上(53%)的枪支是坏的和有其他问题”。这一说法作为核心观点被评论家广泛引用。
衡量其结论是否准确,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史料是否确凿。这可以说是历史学唯一的评价办法。当那些好事的历史学者开始想核实贝勒斯雷斯的研究资料时,他们遇到了麻烦。贝勒斯雷斯称他把所有的数据全记在普通的笔记本上,而他的办公室在5月因一场水管爆裂而被淹,殃及这些笔记本,因此他手头没有有关数据记录。于是,他们又希望贝勒斯雷斯告诉他们原始出处,以便能够核实。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贝勒斯雷斯的说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他说他所研究的40个县的资料都已制成缩微胶卷,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位于乔治亚州的联邦档案中心(the Federal Archives in East Point,Ga)。在发现那里没有这些文献后,他承认自己的记忆有误,改口说他是在全国30个州和县的档案馆查阅的原件,而非缩微胶卷。人们难免满腹狐疑,因为一个历史学者怎么可能忘记自己的研究资料是在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档案中心,还是在全国30多个地方收集的?

后来,贝勒斯雷斯又在自己的主页上公布了一些残存和新收集的遗嘱清单资料,说明自己的确掌握不少有关文献,没想到这一做法被批评者视为欲盖弥彰, 他们又在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严重的问题。对此,他先是承认资料有误,接下来却又说可能有黑客侵袭他的主页,窜改了他的资料。
批评者仍不甘心,利用可以找到的资料进行核对,发现失误惊人。而且,这些失误恰好都是用来作为支持作者观点的证据。以罗得岛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为例,贝勒斯雷斯的书称,1680到1730年,186份遗产清单中,财产主人都是男性,其中只有90份提到了枪支,其中一半以上被遗产清理者评估为“过时和质量很糟”。但至少有三位学者各自独立地研究了同一档案,却发现财产主人中有17人为女性,提到枪支的清单也远比贝勒斯雷斯所称的要多,而且只有9%的枪支是“过时和质量很糟”。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他著作中的失误不论是数量还是范围都是“非同寻常的”。
如果说这些失误还可以找到借口的话,那么作者所引用的旧金山的资料却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他一再强调,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级法院中,他查阅了1840-1850年代数百份遗产清单。在这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这些文献实际上已经毁于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及随后的大火,用旧金山高级法院的负责人的话说,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一位出版过三本有关旧金山地区遗产清单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称,在1880 年以前,并不存在有关遗产清单的正式记录,1880-1905 年的记录虽然有,但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贝勒斯雷斯又改口说自己记性不好, 这些文件应该是在Sutro Library中。但该馆的馆员告诉记者,他们编有1850 年以来旧金山地区所有遗产清单的目录,但都没有提到拥有枪支的情况。这就是说,这些文献不可能成为贝勒斯雷斯研究的资料。旧金山文献并不是唯一一个作者声称用过,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例子。
《波士顿环球报》披露了另外一个蹊跷的问题。由于他的辩解漏洞百出,贝勒斯雷斯所面对学界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他请求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兰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为他辩护。罗斯称,如果贝勒斯雷斯告知其所使用的佛蒙特州的文献, 他会自费去核对这些文献,如果属实,他愿意撰文为他洗冤。出乎意料,贝勒斯雷斯拒绝罗斯的善意。这不能不令人更加怀疑。
原来那些为他的研究大唱赞歌的历史学者,也开始退缩了。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克·拉克夫(Jack Rakov)一方面继续赞扬《武装美国》“提出了美国生活和文化中武器所扮演的作用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遗嘱清单的问题”。但他也承认,贝勒斯雷斯应对他的批评者作出远比目前所作的更为充分的回应。
贝勒斯雷斯还给调查此事的记者10位学者的名单,说他们很了解其研究的意义,也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而不要只注意一面之词。记者用电话联系到了其中的6个人,发现他们或者对其研究工作持负面态度,但并没有指控其编造;或者不再给予赞扬,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反驳说有关的批评是不实之词。
贝勒斯雷斯所在的艾默利大学——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南方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在社会压力下,开始要求他作出适当的解释。该校历史系主任要求贝勒斯雷斯在合适的专业刊物上,对所有的批评做出一项“合理的、规范的、详细的、逐一回应。” 但是,他在美国历史学者协会通讯上的回应,集中在保守派对他的骚扰,而不是学者对其著作的严肃批评。
在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之间
目前,围绕着贝勒斯雷斯著作的争论还在进行。但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明确,那就是贝勒斯雷斯在史料处理上,非常不严肃。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方面的问题,只是认为这是局部问题。因此,2001年出版的平装本中,作了改动,比如删掉了罗得岛普罗维登斯那部分材料。问题现在集中在对贝勒斯雷斯批评是否公允;其次是他的应用史料上的问题是正常失误,也就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还是,性质严重的有意编造?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科勒尔虽然没有指出批评者的具体错误,但是认为,一些批评“出于意识形态的歇斯底里”。“即使贝勒斯雷斯被证明错了,即使他的书存在瑕疵,这仍然是本重要的著作,推动了讨论,就此,我们所有的人也应感谢他激发了对问题的辩论”。但斯坦福大学教授、1997年普立策历史著作奖获得者杰克·拉克夫和其他一些批评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滥用和曲解史料“是个大问题”, 贝勒斯雷斯必须对此负责并作出表态。
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权威期刊《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 Mary Quarterly)即将就《武装美国》的史料及运用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如果学术界最终形成共识,认定《武装美国》是一本有严重缺陷、甚至是作假的书,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艾默利大学校方也不得不表示,一定会严肃处理。
鉴于班克罗夫特奖是美国历史研究最有声望的奖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获奖著作受到如此多的非议。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不得不把那些逐一指出《武装美国》失误的文章及相关文件的资料,整理成册,送给2001年的三位评奖人,请他们明鉴。
这场争论的确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武装美国》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如此器重,显然是因为它证明了美国持枪权争论中,开明派的观点,同样,它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是挑剔,也是因为社会上的保守派揪着不放,学术界对获奖著作的高要求。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编辑挖苦说,“如果历史研究的目的是重建一个与某个人偏见相适合的过去的话,那么,贝勒斯雷斯可以被认定是一个成功。但这显然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只有理解这一点的人才有勇气承认:《武装美国》已经被它自身的不诚实解除了武装”。
如果冷静地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应该说,贝勒斯雷斯在材料使用上的确有创新,特别是利用学者原来所忽视的遗产清单的资料,来研究缺少枪支具体统计资料的枪支拥有问题,是有价值的。对贝勒斯雷斯,问题可能是在最初的研究引起学界高度评价后,他在下意识里急于扩大“研究战果”,产生更大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结果,在有关的材料、特别是遗嘱清单档案使用上,饥不择食,出现严重差错,结果授人以柄,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声誉。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确印证了资中筠教授对学术界的精彩评论:“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贝勒斯雷斯研究枪文化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社会价值所在。历史学家也有权利、甚至是有责任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作出回答。但问题是,如何回答?如何尽可能地祛除个人的价值偏见(Value Free)?如何不受主导思潮的影响和左右?重大历史题材的写作既可以给学者带来一般普通研究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名望,但同样,也可能面临着更为挑剔的批评的、甚至是攻击。当然,学者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现实中,不可能保持绝对的中立和自省,但学者又和普通人不一样,他的职业要求是对真实而非现实负责,对历史而非观念负责,作为现代社会精神文化产品的制造者和历史传统价值的阐释者,他们的研究可能会塑造和改变社会的潮流和观念,因此,对他们理应提出更高的职业伦理的要求。

因此,对贝勒斯雷斯的批评不能全部归咎于保守派的偏见。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为它唱赞歌?在授予它班克罗夫特奖之前,已有学者批评该书的史料问题。出版过英美持枪权概念的乔伊斯·麦尔考姆(Joyce Malcolm)教授就批评说,“贝勒斯雷斯甚至没有提供有关遗嘱数字的起码的信息,而这是构成其枪支稀少论点的基础。而且,他一再作出绝对化的基本判断。但如果你核查他的注释,就会发现一个令人烦乱的模式。它不只是个别的错误或者是与众不同的解释,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误解材料实际的含义,如果这些材料真的存在的话。”显然,他对史料的误读相当严重,但评奖人却视而不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由派学者太受现实的影响,控制日益泛滥成灾的枪支成为他们日益关注的主题,形成他们内心中一个先入之见,或用时髦的话说,一种理论“预设”,一时影响了他们进行客观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学者汲取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