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将数字游戏引入学校教育
【编者按】
孩子们为什么都爱玩数字游戏?数字游戏以及从成功的数字游戏中学到的手段,可以用来如何重新设计学习计划乃至教育体系,并使之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吸引和切实的好处呢?
格雷格·托波,《今日美国》的资深教育记者,在《游戏改变教育》一书中,他探讨了目前美国教育系统中涌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孩子们阅读量的不断减少,而且据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在余下的一生中都不会再阅读任何书籍。托波尝试通过观察数字游戏作为一种新体验和新机制,是如何被引入教育改革的领域,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来讨论美国教育的现状和前景。
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一章《一种终极的放纵:我怎么会对视频游戏感到好奇》,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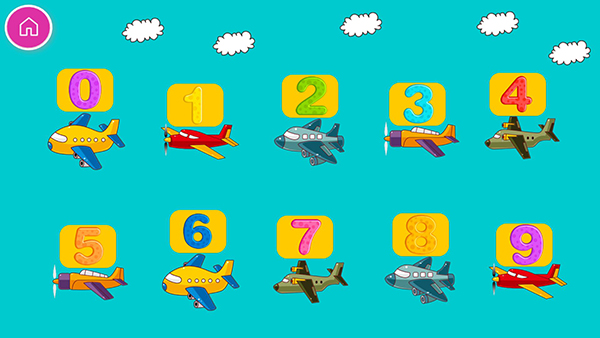
我的女儿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几乎完美无缺的孩子,考试成绩全优,痴迷大提琴,还是个数学天才,念高几个年级的课程也不在话下。她自信满满,打算直升大学,简直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五年级生的模范样板。如果连这样的孩子都不喜欢阅读,那阅读真的还有机会吗?
我的女儿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每个房间都摆放着书籍,厨房、厕所也不例外。在她童年时代头几年,我曾是她的启蒙老师,因此我搜罗了一箱又一箱的儿童读物,并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她和她妹妹的房间里。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周日,我们都会去巴诺书店,在那用餐、看书、买更多的书带回家。在我们家里,如果不事先把厨房餐桌上的报纸杂志清理开,就没法开饭。我们逾期未还的图书馆借书,比大多数人的家庭藏书都要多。公平地讲,我们或许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是,在六年的学校生涯之后,但凡有所选择,我的女儿就不愿再拿起一本书来了。她并非个例。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在他们余下的一生中都不会再阅读任何书籍。作为一个记者,我开始寻找究竟谁该为此负责。
看起来,她生活中几乎所有影响因素都有责任:父母、老师、朋友、电视、音乐。也许还因为她作为躁动不安的狩猎者—采集者种族的成员那与生俱来的进化习性。又或者,仅仅是或者,阅读——持续不断、聚精会神、平心静气、深思熟虑的阅读——本身已经变得太困难了。我开始持续研究,并且发现孩子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能接触到书籍——1954年时,公立学校图书馆的人均藏书量是3本;到2000年,人均藏书量则是17本。虽然藏书量增长了,但阅读这件事看起来却丧失了吸引力。四十多年来,尽管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几乎都在增长,但17岁年龄段的阅读能力却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不仅如此,在1984年和2012年的两次调查中,17岁年龄段中认为自己“从未”或“几乎从未”为乐趣而阅读的比例翻了三倍。
事实上,我不是唯一一个关心阅读将何去何从的人。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注意到,浏览万维网并通过超链接搜寻信息,这一新近养成的习惯几乎已经让他丧失了完整读完一本书的能力。他在担忧人类已经从“个人知识的培育者演化成了电子数据森林中蛮荒的狩猎者和采集者”。艺术家及作家大卫·特伦德在追寻为什么他8岁女儿会有“关于书面词语的神秘问题”,他说:“在她人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并不需要阅读。”她的世界被图像、媒体和交互技术驱动,这一切都是如此诱人,可以轻松接触,以至于学习如何阅读“感觉就像是个由成人和学校发明的阴谋”。

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阅读习惯的研究显示,美国人里收入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加热爱阅读,但即便这部分人的统计数字也在危险地减少。2005年,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温蒂·格瑞斯伍德开始提出,就像“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或“喋喋不休阶级”(chattering class)一样,有一个小规模的、精英化的“阅读阶级”(reading class)正在涌现;即使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阅读,但这个阶级仍旧非常重视读书。温蒂写道,目前尚不明了,读书是否将会成为一种令人景仰、阳春白雪的技能,或者像刺绣和弹奏竖琴一样的“与日俱增的神秘爱好”。她发现,尽管受过教育的群体还是读书最多,但是其中相对年轻者的阅读时间在急剧减少,减少趋势跟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她预见到将有整整一代人拥有阅读能力但就是不去阅读。这跟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后果其实是相同的。
是教育出了问题吗?资深教育工作者凯里·加拉赫认为确实如此。他在2009年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术语“阅读的自杀”(readicide),来描述他看到的在全美国学校中正发生的事情。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他也对学校把应试教育摆在真正的学习之前感到苦恼不堪。但他也发现,在行政管理层要求之外,老师们对那些重要的书本展开了“过度教学”(overteaching)和“不足教学”(underteaching)。老师们讲授教学内容过于迅速,把学生们丢进了“记事贴、页边注释和学术期刊的汪洋大海”。加拉赫总结说,在一个本应培育孩子们对阅读的热爱的地方,实际却扼杀了这种热爱之情。“动机并没有问题,”他写道,“是我们的实践出了问题。”
古怪的是,这场危机发生之际,却是儿童读物空前蓬勃发展的时期。此刻只要你环顾四周,就可以看到孩子们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大部头的书籍,那些我们这辈人可能认为无趣的精装本小说。先是《哈利·波特》系列,以及稍晚几年的《暮光之城》系列都抓住了孩子们的心。在2008年,七部《哈利·波特》占据了我所供职的《今日美国》图书排行榜前九名中的七个席位。而到2010年,四部《暮光之城》已经在图书榜单中盘踞了两年。当我与知名儿童小说家M.T.安德森见面时,他告诉我,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纽约从事童书出版工作,那会儿如果他推荐每本厚达700页的儿童小说系列的话,一定早就成为曼哈顿市中心的笑柄了。他说:“当时普遍的常识是:‘绝不会有孩子去读那样的书,那太荒唐可笑了。’”然而如今,那些七八百页的书籍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畅销书。“每个孩子都在阅读这类总计超过数千页的巨著系列”。
因此,只要有合适的书籍,以及社交影响,孩子们还是会阅读大量的印刷读物。那么儿童的阅读量真的在减少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取决你如何发问,你将得到不同答案。事实上,“阅读量的减少”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如何去测量这个数量?是以阅读的分钟数计算?还是按阅读的页数计算?或是看看印刷那些吸血鬼小说消耗了多少磅纸浆?
最终,一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出现了:如今孩子们到底在关注些什么?
我发现,他们几乎关注每一件事:书籍、音乐、电影、电视、时尚、舞蹈、科学、历史、经济、政治、摄影。他们也关注彼此。他们什么都关注,但就是不关注学校,以及那种让他们条条块块地切分学术科目的方式。生活中那些神奇的设备帮助他们通往一个崭新的世界,也带给他们思考世界的新方式。我们生活的时代,被教育家威尔·理查德森称为“丰裕时刻”,这让我们的孩子总能以自己的方式,随时接触到几乎所有事物。学校看起来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视频游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典型地展现了这种“丰裕”。在我目光所及之处,游戏正在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力量。游戏让年轻人一起欢度时光,相互发起挑战,释放压力,学习新东西,并最终找到他们的社会定位。很多时候,孩子们就是喜爱游戏本身;另一些时候,他们欣然接纳的是围绕左右的亲合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总是在谈论和写作游戏相关内容,一起分享游戏修改方法和新闻,还通过设计一些困难得让人惊掉下巴的新关卡来彼此挑战。
许多孩子通过玩游戏来面对麻烦事或挫折感,还有很多孩子通过游戏来宣泄冲动、排解悲伤。我遇到过无数男孩,其中很多来自离婚家庭,都会跟父亲一起玩游戏,有的共处一室,有的远隔千里。我还遇见过一个名叫艾瑞克·马丁的大学生,他曾在高中一年级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厌食症,住院治疗一个半月。在康复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简称MMORPG或MMO)——《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简称WOW)。他说这个游戏拯救了他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他这么想,在轻博客tumblr上有一个名为“游戏怎样救了我的命”的页面,详细叙述了“视频游戏那改变人生的力量”。
视频游戏已经变得令人惊异地栩栩如生、精妙复杂,以至于催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玩家们正在通过许多方式用视频游戏学习并影响现实世界,而这些方式是游戏开发者原本未曾想到的。游戏正在重新校订玩家对生活的期望,从需要手眼配合的《吃豆人》(Pac-Man)到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东西。视频游戏批评家汤姆·比赛尔写道,当他访问伦敦时,仅仅凭借自己玩《大逃亡》(The Getaway)这款开放世界式驾驶游戏的记忆,他就知道了从特拉法加广场到达大英博物馆的路线。畅销游戏《刺客信条》(Assassin’s Creed)的创意总监亚历克斯·哈钦森告诉我,他收到过一些玩家来信说因为玩了《刺客信条2》而专程探访了“水城”威尼斯。还有些学生来信说凭借着在游戏里学到的有关波吉亚家族的知识而高分通过了考试。亚历克斯·哈钦森说,没有人会把这个被划分为成人级别的游戏系列和教育类游戏搞混淆,但这些玩家反馈却证明,历史可以是“生动鲜活、紧张激烈、引人入胜的,是让人牢记不忘而不是用过就丢掉的东西”。

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人员科特·斯夸尔在2001年出版的《视频游戏与学习》(Video Games and Learning)一书中,回忆了高中历史课上老师有关西班牙殖民史的提问。在一次“神游天外”之时,老师问是否有人知道,欧洲不同国家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船舶。斯夸尔举起了手,就像对着教科书念那样说:西班牙有可装载黄金的大型加利恩帆船,“法国人大多开着三桅帆船(barque)。荷兰船是福禄特帆船(fluyts),英国人开着商船(merchantman)。如果你看到船上有舰载舢板(pinnace),那就是法国船、荷兰船,还可能是条海盗船”。斯夸尔进一步解释,荷兰人“是精明的贸易者,他们在海上的领土并不算太宽广,尽管库拉索岛是一个极佳的贸易基地”。斯夸尔这番即兴发表的学位论文般的演说,甚至让一个必须进行的课堂测验推迟了。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他们都很想知道斯夸尔哪儿来这么些知识。“这其实是我在我的Commodore 64电脑上花了很多时间玩《席德梅尔的海盗》(Sid Meier’s Pirates!)的结果”。
英国记者吉姆·罗西尼奥尔对游戏的魅力提出了最佳解释。游戏是一种“贪婪的”媒介,它从音乐、漫画、小说、电视、雕塑、动画、建筑、历史等诸多领域吸取养分。罗西尼奥尔写道,游戏是“一种终极的放纵(ultimate decadence)。它像地球上其他事物一样,制造成本高昂,完全根植于人们对愉悦的渴求。它精妙而复杂,激发种种体验,却不像毒品和纵情放荡那样留下太多副作用。它是对兽性冲动的放纵,却并不产生真实的暴力或不知羞耻的堕落。”
换句话说,游戏也是最适合引入学校教育之中的。
当我刚开始迈入游戏领域的时候,我发现老师们也正尝试着把游戏偷偷地带进课堂教学中,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够提高教学质量。令人欣慰的是,我发现首倡这种风潮的老师们不但还在教学岗位上,而且成效不错,更渴望与人交流。最初我打算跟踪每位教师的进展,掌握他们的行动,对每个人进行访谈。但我发现,这样的老师太多,我根本访谈不过来——事实上这样的老师比我曾交谈过的所有人的数量还要多。即使现在,我几乎每天都还能碰到一些我本该了解、但却没机会认识的游戏设计师和教育者。我发现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投身此领域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有多热爱游戏,而是由于他们热爱孩子,并且希望给他们更美好的东西。于是后来,我已经习惯了某人凑过来对我说:“不,我并不是个出色的游戏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