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玮评《禅的历史》︱花朵、树叶与真理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乃禅僧最常拈举的一则话头。相传达摩自西徂东,引来印度禅,是为中土禅宗初祖。“祖师西来意”即达摩所授禅宗要义。这样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回答却五花八门,或曰“问取露柱去”(石头希迁),或曰“与我将床子来”(沩山灵祐),或曰“庭前柏树子”(赵州从谂),或曰“久雨不晴”(云门文偃)……总之是顾左右而言他。何以如此?皆因禅宗——严格说来,马祖道一以降禅宗——修行的终极目标,质言之,即绝对专注于当前一境。而一问达摩之意,注意力便投向过往,脱离了当前,故须截断、扯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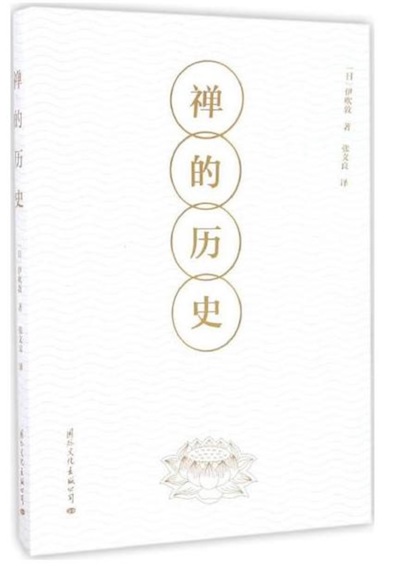
伊吹敦《禅的历史》(张文良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12月)指出,日本禅从中国接受的,主要是宋朝禅,正属马祖道一系统。
本书综合中国与日本禅宗,作一连贯的历史叙述,凡分三部:禅的足迹(中国)、禅的足迹(日本)、禅的现状。禅宗在古代亚洲流布颇广,又传入朝鲜、越南等地,这些概置不论;现状部分,更只单述日本禅宗,可见著书宗旨实在于,为本国鉴往而知来。
伊吹先生认为,达摩“二入四行论”同后世禅宗迥然有别,但已显出鲜明的如来藏(佛性)思想。由是梳理中土禅史,围绕怎样修证佛性,观察到两种相反走势:内向化与实践化。“二入”包括经思考悟入的“理入”、在事上悟入的“行入”。后者又细分为四种,谓之“四行”,包括报怨行,受苦时自念系以往恶业所致而“甘心受之”;随缘行,得意时自念系以往善缘所感而“心无增减”,等等(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六)。“理入”是内向化的,“行入”是实践化的。
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提倡“守心”;北宗神秀承流接响,提倡“观心”,均为“理入”之延续。“理入”须“凝住壁观”,借助打坐来开悟,道信、弘忍、神秀等人亦然。坐禅是特定时空的特定修行法,非随时随处可为,与日常生活界线分明。及至南宗神会提倡顿悟,一举否定打坐修行,内向化走势遂告消歇。直到南宋临济宗形成公案禅(看话禅),曹洞宗形成默照禅,前者以参详昔人公案为入道手段,后者重拾坐禅,这一走势方稍稍复振。
中唐神会以还,实践化走势占据主流。之前达摩教人“行入”,弘忍门下禅师参与农业劳作,禅宗早和日常生活相联结。及至神会主张顿悟,修行无须特殊方式,但从行坐言笑间得道,日常生活乃成为禅僧经验的唯一内容。不过,神会要求在日常中,体悟超越日常之上的“知”,仍未尽然认同日常。马祖道一更进一步,标举“平常心即道”,彻底否认超越性理念,始与日常生活贴合无间。在另一篇文章里,伊吹先生因而称其为“禅宗之完成者”(《马祖的思想与时代精神》)。
在著者看来,宋元之交蒙哥可汗座前,佛教与道教的公开辩论(1255—1258年),标志着二教信徒“完全失去了对各自宗教固有教义的坚持”,嗣后再无突破性发展。故南宋以前,内向化与实践化的消长起伏,足可概括中国禅宗的思想变迁。就每章末所列文献观之,本书讨论中土禅史,多参考日本学界成果,然而在若干问题上,也不难窥见中国学者的影响。譬如断言六祖慧能《坛经》曾被神会一派“大幅度改变”,淡化慧能的历史地位,显然采纳了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的特见。又如强调牛头宗的重要性,则系印顺《中国禅宗史》的发明。伊吹先生担纲是书日译,对这一观点印象极深(参看日文本译后记)。耐人寻味的是,印顺法师勾勒牛头禅思想的整体结构:道本虚空,无所不在。因为虚空,所以不必刻意修证,“高卧放任”便是行道;因为遍在,所以连无情的草木之类也蕴有佛性(《中国禅宗史》第三章)。不事修行恰合乎实践化走势,原可织入叙事主线,伊吹先生却只字未提,仅举“无情佛性”一点为说。他大约依然希望将中国禅的成熟,归功于南宗神会、马祖一系。至于后一点,则确为牛头宗的特色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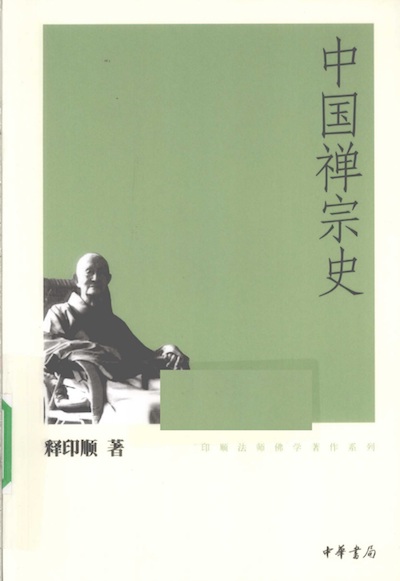
日本奈良时代,禅宗已然东传,以北宗禅为主。平安时代,最澄融合圆、密、禅、戒四种教法,其中禅学除北宗外,又加入牛头禅的成分。但这时对禅的接受,尚停留在非系统、不自觉的地步。平安末年山雨欲袭,人心不宁,禅的现实意义首度突显出来,下开镰仓时代禅宗兴起之先声。
镰仓前期当中国南宋,伴随中日僧人往来,宋朝禅大举涌入,临济与曹洞之争也延烧至东瀛。两宗离合变化,构成日本禅史一大线索。临济宗特征相对稳定:修公案禅,向当权者弘法。江户中期白隐慧鹤把公案按内容分类,重新编排,更“将公案禅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相比之下,曹洞宗的走向则一波三折。镰仓前期,道元学成归国,举以授人,修默照禅,传法取精英主义。镰仓后期,莹山绍瑾一反其所为,导入公案禅,向普通民众弘法。前者已有接近临济之势,后者则为曹洞宗的新特点。下及室町中期,即在曹洞内部,公案禅也占了上风,几与临济泯然无别。至江户时代,一方面向道元回归,重修默照禅,运用公案日少,复与临济分流;另一方面,却又和后者共同推动学问研究长足发展,偏离一直以来的民众路线。明治维新后,现代禅宗继续学术化进程,著者批评这与信仰易生抵牾。倘使问其意见,大概从镰仓到江户时代,是日本禅最具活力的阶段。
伊吹先生并非信徒,可是服膺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注重日常世界(《社会学视角的禅宗研究——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伊吹敦教授访谈录》),实践性格明显。临济之公案、曹洞之坐禅,都偏于内向化,站在他的立场,未必足观。本书写到日本禅的成立,专辟“日本接受禅的问题点”一小节,下了一个总判断:“在中国,禅宗创立的契机是向日常回归、力图以俗语来进行思想表达,而日本禅宗的情景则正好相反。”态度不言自明。唯有曹洞宗向庶民说法,为其所许。回归日常生活,普济众生,也是他寄望于将来日本禅宗者。
前言交代,本书原计划通论禅的历史、思想、文化,后因兹事体大,乃先写出历史之部,单独付梓。尽管著者努力“从思想史的视角撰写”,统观全书,仍觉历史的解释有余,思想的解释不足。日本禅为何承续马祖道一系的宋朝禅,而非其他?本书答案是,镰仓时代禅宗突起,适逢南宋禅学流入,因缘际会使然。这是历史层次的理由。然而不妨追问,既然镰仓以前,北宗禅与牛头禅早已进入,为何日本禅不表现为旧禅学的自微达显,却表现为新禅学的拔帜易帜?对此,还须给出思想层次的理由。
著者叙及平安时代,注意到比叡山天台宗本觉思想之确立,“不仅对佛教而且对整个日本文化都带来很大影响”,可惜语焉未详。本觉思想倡言众生当下便是开悟的显现,不假外求。所谓当下,无分善恶;所谓众生,包含无情草木,具有强烈的肯定现实意味。镰仓时代,“不问净土、禅或日莲系,新佛教全体的基盘——也就是新佛教的祖师们都是出身比叡山,且接受比叡山系的学问”(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此乃日本禅生长的思想风土。反观马祖道一,绝对专注于当前,不作他想,必然对当前无所拣择,故同样有“不取善,不舍恶”之论(《祖堂集》卷一四)。不过,他虽无分善恶,却分有情无情,未言草木可以成佛。后一说为牛头宗所独有。马祖禅与牛头禅,同本觉思想各有契入处。但本觉思想无条件认可当下,推至极点,便消解了修行的必要,镰仓新佛教又有所反思。牛头宗唐末已渐衰歇,思想未及新变。而马祖禅传衍至南宋,创设公案禅与默照禅,提供具体的修习方法,正可对治本觉思想之流弊。只有在这个层面方能说明,接受宋朝禅,何以成为镰仓禅宗的最终选择。

本书横跨中日,纵贯古今,是禅宗史写作的一项尝试。台湾诗人杨牧编译《叶慈诗选》,有首《睿智随时间》,这样写道:“树叶虽然很多,根柢惟一。/青春岁月虚妄的日子里/阳光中我将叶子和花招摇;/如今,且让我枯萎成真理。”叶芝(台译叶慈)向往“超自然的世界”(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他的真理,要待花朵与树叶枯萎后浮现。而依马祖道一以降禅宗之见,会心当下即是。真理就在日常世界之中,就是禅在中国的开花,在日本的散叶,是每一次的滋长甚至——枯萎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