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谈《唐代财政》:奠定西方唐史研究的基础性学术著作
【编者按】2016年5月,中西书局出版了英国汉学家杜希德先生的《唐代财政》一书的中译本,本书责编李碧妍博士特邀北京大学教授、杜希德先生弟子陆扬做了一期访谈。近日,“中西书局”微信公众号(zhongxibook)首次发布了访谈视频。经授权,澎湃新闻整理了访谈的文字稿,并经出版社和陆扬教授审定后,与读者分享。

李碧妍:大家好,我是中西书局的李碧妍,也是我们新近出版的杜希德教授的《唐代财政》一书的责编。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杜希德教授晚年最重要的弟子,陆扬老师,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教授,给大家做一个关于此书和杜希德教授的访谈。大家知道,杜希德教授曾经任教于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陆老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跟着他读唐史的,那么我们首先请陆老师介绍一下杜希德教授大致的生平情况。
陆扬:非常感谢碧妍的介绍。我也很荣幸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跟杜希德教授学习的体验,同时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杜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也是唐史甚至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唐代财政》的中译本终于出版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杜先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或者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我个人当然很荣幸,在他晚年有机会跟他学习,虽然我跟他学习的时间不能算很长,但是我跟他还是有相当的接触。所以对杜先生的学术,他个人对研究的很多贡献,等等,以及对普林斯顿中国学研究发展的贡献,都算是有一点了解,所以今天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也很荣幸。杜先生他实际上早年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但如果就唐史研究来说,他和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那一代,基本上他们的研究都属于有开拓的意义,但是同时,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当然不能完全说是自学,但基本上道路是自己开拓出来的。

杜先生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但他的老师相当有名,也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汉学家叫做Gustav Haloun(古斯塔夫·哈隆,汉名霍古达),是一位德裔的学者,Gustav Haloun虽然在汉学上颇有造诣,但实际上并不是唐史的专家。在这个意义上,Gustav Haloun对杜先生学术生涯的发展并没有非常关键的意义。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回国这几年看到季羡林先生,当然这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前辈学者,季先生写的《留德回忆录》,他里面就讲到他在哥廷根的时候,关系最好的西方朋友就是Gustav Haloun,当时Gustav Haloun还没有去剑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因缘。但是我想回到刚才的主题,就是杜希德他本人的求学经历更多是他自己探索出来,当然这中间也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恰恰是他早期学术生涯发展的阶段正好是西方汉学出现重大转变的时期,就是从更倾向东方学、汉学的早期传统,慢慢转向对中国历史整体的了解,他要追溯的并不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要关怀整体的问题。而他恰恰属于那个generation那一代的,除了他之外,包括其他一些剑桥、英国的学者,非常重要的像蒲立本,几乎和他是同时代的,而且在早年的学术生涯发展的方向也很类似,关注的问题也很相似,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这本书出版比《唐代财政》稍微早一点,但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两本书看作是奠定西方整个唐史研究的基础性学术著作,在他们之前,严格来讲,西方没有所谓的唐史研究。我曾经看过在此之前最重要的西方学术杂志,绝大部分杂志很少有唐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偶尔会出现一两篇,当然关于唐代的文章是有的,但真正关于唐代历史的重要问题的分析,可以说凤毛麟角。但是,在杜希德和蒲立本教授他们念博士到早年任教这一段,大概十年时间以内,突然一下出现一个可以说是高峰,这一点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于杜希德先生他早年的学习我刚才说了,Haloun本人对他帮助有限,但是并不等于说英国的学术环境对他没有帮助,事实上是有的。比如Arthur Waley(阿瑟·韦利),很重要的翻译唐代文学和中国、乃至日本古典文学的英国翻译名家,他的很多译作我相信对杜先生是非常有影响的,说起来杜先生晚年他一直专注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重新考证、研究白居易的诗。这里面我想有两层,第一层就是Arthur Waley当年译的白居易的诗影响非常大,他写的关于白居易生平的著作到现在看都还是有它的价值,虽然我们今天的研究已经远远不是他那个时代,但还是有价值。另外我还想讲,杜先生实际上很早就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是一般不太受到注意的,但实际上非常重要,在英国乃至于欧洲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一段,实际上中国的学术已经开始影响到西方,当时杜先生曾经想过要在剑桥念完以后,要到中国来跟陈先生念,他已经是下了决心要去,结果后来没办法碰到49年的特殊情况,他就只能转道去日本,他就跟了日本最重要的研究唐代法律、社会制度的学者之一仁井田陞,给他的影响非常大,使他能够走上一个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等以往西方学者不涉足的领域,相信这个日本学术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还有一个对他影响也很大的是穆勒,就是后来和伯希和一起翻译《马可波罗行记》的重要学者。这可以说是他早年的学术导师。
另外杜先生成名很早,基本上从他念完博士不久,后来他就去了英国很有名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很快就成为教授,不久又回到剑桥,所以他在剑桥待的时间非常长,一直到他后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去了普林斯顿,他早期的生涯几乎都是在剑桥度过,所以他和剑桥的学术关系也非常密切。之所以他后来会成为《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我想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也是因为他在剑桥大学对中国史研究的推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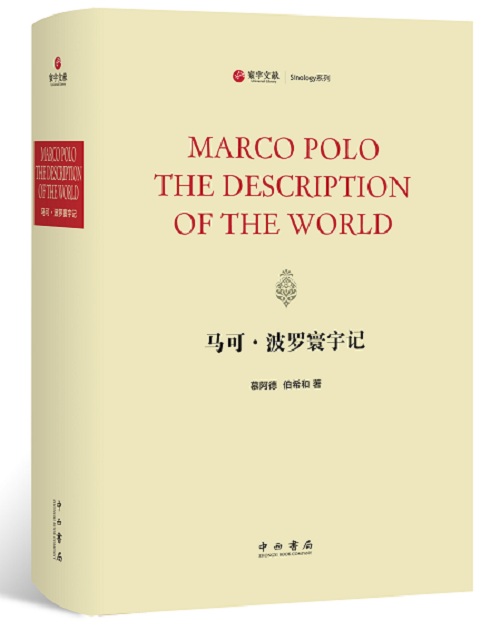
李碧妍:是不是您觉得,杜希德先生的成功是因为在一个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开始对唐史和中国史研究有一个新发展的推动作用下,他受到他们影响,或者他们在互动的情况下,才对他后来的成长或者是对他在唐史上的突出贡献,是有一定帮助的?
陆扬:那这么说就是这几个因素都有。当时正好大家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开始落实到比较大的问题上,这几乎是在欧洲很多地方,乃至于美国很多地方同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他是受这个影响。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是很重要的推动者,实际上他本人也推动了,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出现,我想我们不能够只是在中国文史的范围内去理解。在这之外还有整个历史研究的变化,因为他的研究受到很多西方学术的影响,比如那个时候有Etienne Balazs(汉名白乐日),很重要的匈牙利裔学者,比如法国的学者像Genet谢和耐等,通过敦煌文书都开始注意到中国的社会经济等等问题,对杜希德影响都很大。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当时在英国剑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杜希德先生和李约瑟的观点不一样,比如李约瑟早年出版了最早的第一、二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杜先生就写过批评性的书评,所以他们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更倾向于把他们看作一个潮流里不同的变化。而且他在写《唐代财政》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所以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李碧妍:我们对杜先生的了解,之前他的《唐代官修史籍考》也翻译出版过,可能我一直觉得他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做的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担任此书的责编以后,我是没有想到他会选择唐代财政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我想请您稍微谈一下,他当年选择唐代财政这个题目是否有一些缘由或个人的偏好,或是时代背景?
陆扬: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询问过杜先生,应该说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推测,我觉得他选择这个题目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我的了解,杜先生很少选择一些我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关键性的史学课题,他一生写的论文也好,专著也好,包括他对别人的关注、评论也好,一般都落实在重要的史学课题上。我们应该想象到在他写《唐代财政》的时候,西方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唐代社会经济的完整研究,当然关于其他断代的,比如先秦两汉或者明清,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也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在很多方面,他的研究不仅是带动了唐史、中古史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很多断代,比如他对宋代研究的推动非常大。因为你要研究财政就要研究制度,你要研究制度就要研究社会结构,这两点你是逃不掉的,这就涉及到你要了解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你才能理解财政制度是怎么落实,它是怎么变化的。正是因为他重视这方面,所以他对于后来的社会史研究有重大的影响,我想之所以之后大家都认为他做《剑桥中国史》的主编非常合适,恰恰是因为他担任《剑桥中国史》主编的那一刻,正好是西方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也特别受到重视。他恰恰在这方面对前面、后面的研究都有很大影响。
当然他的影响绝对不只是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他对政治史也非常敏感,而且他对政治史的理解很有自己的特点,虽然他在这方面的论著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很突出。比如说《剑桥中国史》里关于玄宗的那一章,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一章就是他写的,后来还得到了蒲立本先生的称赞,蒲立本先生在一篇日本发表的书评里特别表扬了《剑桥中国史》里的这一章。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蒲立本先生和杜希德先生的个人关系并不密切,所以他能够超越他们个人的关系来公开表扬,而且玄宗的这一章恰恰是蒲立本先生最擅长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西方学者很优良的学术风气,他们可以超越自我和个人的芥蒂,在学术上认可对方,这也很了不起。
回到刚才你问的那个问题,我想他除了对中国史、社会史的关注之外,还受到新资料,就是敦煌文献的影响。日本的仁井田、法国的谢和耐他们通过这些文献研究唐代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方面对他刺激很大,包括Etienne Balazs对这方面的研究,对他启发很大。但是他们的研究,比如谢和耐主要还是在佛教社会经济方面,仁井田更多地关注唐代的文书,来了解唐代的社会财政制度等等。但是杜希德先生这本书其实关注点不太一样,他是真正关注中央财政制度的建立以及演变。他同时具有两个很重要的贡献,在早年他是和仁井田他们类似,通过文书去具体了解地方的财政制度是如何落实的,同时他又有一个很整体的看法,对唐代作为一个帝国怎么去建立它的财政体系,这个体系存在哪些特点和先天性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就是先天性的毛病后来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情势下怎么调整,这个我觉得他是很能把握的。虽然他这本书出版很早,远远早于这类书出现在中文世界里的时间,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像鞠清远这类,但是跟他的这本相比,无论在历史的视野和深度上都有差别,当然后来唐代财政作为一个领域在中文世界可以说发展得很快,但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
李碧妍:我也一直想知道,您的研究领域和他不是很一样,不过有一部分有点交叉。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可能在中央层面、宏观层面的把握和解读上,其实和杜先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那么具体来说,他对您去普林斯顿以后研究唐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陆扬:这个当然说来话长。我是觉得杜先生对我个人来说,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我记得你刚才提到,杜先生是少数西方对制度特别关注的。确实,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弱项,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的强项,就是制度史的研究,当然应该这么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的变迁和复杂性,关注不如中国学者那么密切,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就是我们可能把制度看得过于静态等这类问题,这个我们不去讲它。杜先生他这个方面确实是一个特例,他对制度的变化、对复杂性特别有了解,这确实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方面对我都是有影响的。另外我觉得他对历史非常敏感,我到普林斯顿的时候他应该是临近退休了,后来他身体也不太好,我记得到那里是1991年开始跟他念书,当然在这之前我跟他已经有接触,很幸运能够跟他有保持联系,91年开始,他大概到我资格考试时退休了,严格来讲我跟他念书也就三年的时间,时间应该并不长,当然之后我们也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退休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回到剑桥,但是他每年都要花一定时间在普林斯顿,这样我们也有机会有很多的交流。
他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我跟他念书的时候,他当然是典型的剑桥的学术风气,他并不是那种死板的给你上课,他自己编过大量的关于唐代文献的指导性读物,有些是没有出版的,他在电脑里存了大量的,有些是作为研究生的读物。但是我跟他念书的期间基本上都是读书课,我印象中只跟他上过一门研究课,其他都是读书课,就是我自己阅读,然后每周跟他谈。我确实受他影响,他提出的一些史学问题,包括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可以说我读得都很仔细,我关注的跟他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更关注政治文化等等这些方面,但是他的财政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他跟当时一些东亚的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把财政的复杂性放在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脉络里。实际上应该说《唐代财政》这本书是他早年研究的一个结晶,在这之前他发表过大概有二三十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有些文章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在这本书里,他的成果,有些是在背景里面,你必须要了解他的学术脉络才能知道两者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他写过很多关于廉政的考察,还有屯田,所有这些都是唐代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重要的财政策略,包括很多我们现在讨论得很深入的问题,当时都被他注意到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要想到他在注意到这些问题时,完全没有其他人关注这些问题,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能发现这么多问题,而且都能深入。
我后来选择课题之所以没有往这方面选择,就是说我发现有很多这方面的课题他都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不想重复任何跟他有关的问题,完全避开了他的领域。当然不是说我都同意他的这些看法,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觉得重复别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吧。

李碧妍:其实我也比较好奇一点,您原先是做佛教史研究的,后来又转到唐史研究,其实您中古佛教这块的研究一直也没有放弃掉,包括现在也一直是在做的。那么这两块研究您如何很好地协调?包括您的老师对您这两方面有什么看法和态度?
陆扬:这个说来很有意思。其实我当时之所以能够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这之前我的学习没有任何的学位,这是一个到今天来讲很不可思议的事,主要是两位在普大任教的先生,他们对我抱有某种信心。一个是余英时先生,他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我的兴趣是在中古,他特别去请杜希德先生跟我接触,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两位,他们两位跟我的谈话让我个人觉得投身于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他们也了解我的背景,我在此之前实际上对唐史没有什么了解,当然我中学就开始读陈寅恪先生,但是应该说这些阅读本身,我并不认为让我变得专业,所以我在这方面起步是比较晚的。这方面他们两人都了解,我之前关注的主要是佛教史、中古佛教史这样,实际上杜先生对佛教史,尤其是佛教社会史,他做过唐代佛教寺院很多方面的研究,实际上他对这方面很关注。而且他的训练,虽然他不是宗教史方面的领域,但这方面的素养非常好,所以最初我去的时候他们曾经问过我,假如我继续要在中国佛教史或中古佛教史方面深造,完全可以选择这方面的课题。而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奇怪,我之所以选择他们,就是不要重复我以前的,我刻意要避免我以前学的,如果要走一条比较方便的捷径的话,我就去选一个佛教的课题,当时有很多课题可以选,可以写一个比较像样的博士论文。但是我刻意选择,而且我在求学那几年,基本上刻意回避任何跟佛教有关的,目的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学历史的,我不是说佛教不是历史,就是说我既然要选择中古史的另外一些方向,想在另一些方面有所深入,这是我当初的一个设想。
所以我最后选择的题目跟杜先生既有关系又有差别,我选择了一个实际上他本人非常关注,他也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在我看来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又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关怀。所以在那个背景下我最后决定要选择那样一个题目,那个题目我现在回想起来选择得可能并不是很妥当,那个题目有点大,花了远远超出我原来预计的时间去消化它。到现在我还在摸索之中。
李碧妍:刚才的那些谈话,您是不是觉得对现在高校的学生有一定的帮助?就是说未必是导师特别喜欢的领域自己就一定要去做,或者说可以去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但是一定要是自己比较感兴趣或是比较符合自己性格的方向。可能您在美国的这些经历,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导师比较尊重您的一些选择,而您可能自己也比较明白自己想做一些什么。
陆扬:应该这么说,因为西方的学术传统一般都比较尊重个人的选择,当然和导师的关系必定要在某些方面能给你很关键性的指导,那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就个人课题的选择、方向的选择上,这些都是很自由的。
有意思的是,其实他们虽然很支持我的选择,但是我记得当年开题的时候,他们提过很多很尖锐的意见,他们提得非常准确,包括余先生也好,杜先生也好,他们平常都很鼓励你,但是在学术场合他们会给你提非常尖锐的意见,当然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印象还非常深刻,开题报告那一次可能是我在普大从求学到任教中最让我觉得惭愧的一次,就是自己选择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当然实际上时间也很短,也不太能够容许我。现在回想起来即使给你一年的时间,说不定你还是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为那个课题本身是大家没有探索过的,所以也没有以前的门径可以依靠,完全凭着一些史学的感觉,当然和今天相比感觉差得很远。但是回过头来说,这种既温和又尖锐的方式还是很符合西方的特点。
其实说到我个人最后的选择,我个人感觉我是一个比较窄的人,我关注的东西很少。可能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我的阅读很广泛,实际上不是,我只关心自己关心的,当然可能那个问题是比较重大的,但是我所有阅读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那个,很少超出那个界限。所以我跟很多很优秀的学者相比,他们的阅读范围要比我广泛得多。
李碧妍:既然我们谈到阅读,我最后想问一下陆老师,您平时是一种怎样的阅读方式?平时喜欢看哪些和专业方向比较相关的书?
陆扬: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其实我是很不会谈自己的读书经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读书经验,因为也不是按照预期的计划来进行的。但是我主要的个人感觉是,我基本上以我研究的问题作为中心,然后从那里边辐射出去。当然大家可能说只读和你关心的学术问题有关的书籍显得很狭隘,但实际未必是如此,一个史学问题可以涉及的面非常广,可以涉及到各种方面,有的甚至你没有想到会对你有帮助的书籍、知识,也会突然变得非常关键,这种经验对我来讲是经常性出现的。
但这个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现在,尤其像我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无书不读,当然不是真无书不读,就是读的内容很广泛,兴趣也很广泛。但是进入学术的领域以后,慢慢就训练自己,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是加深你的深度,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方面的兴趣固然陶冶性情等等,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回头想也有遗憾的地方,学术研究就是把你原来的爱好变成专业,你的工作实际上就没有一个分界,所有的读书都变成为了那个目标。这样的话我相信,实际上有很多非常值得阅读的书籍,你就无形中只能放弃,只能选择先不去读它,毕竟时间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