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杨国强:现代化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编者按】7月4日上午,在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的办公室,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4年12月版),算是一次小型的读书会。小扣小鸣,大叩大鸣,我们整理了部分对话,杨国强先生又对初稿从头捋了一遍,几乎等于重写。因篇幅较长,兹分两次发布。本文是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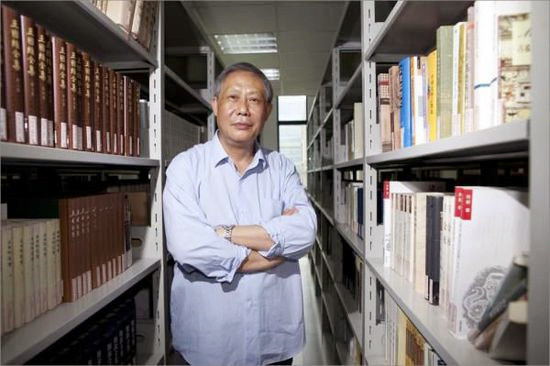
艰难时世中的情感与理性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谈到清末民初严复、梁启超这一代人在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有更激烈的批评反思,民国以后感觉像文化回归线一样对传统重新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您在书中谈到:“西法西学所造成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撕裂,其实质所在,是想要的东西和割舍不了的东西之间撕裂,从而是富强和价值之间撕裂。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们是更早而且更深地感受到了撕裂之苦痛的一群,并在苦痛的牵挽之下回头转身而划出了一种人生的否定之否定,他们因之而成了西潮的回澜。”这段话写得特别精彩,把这一代知识人的“精神史”写出来了,于此就想到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谈到这一代人,他认为梁启超、严复这一代知识人思虑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世界时对于如何处置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极为复杂和暧昧的,理性上认为儒家文化传统无法应对所谓“三千年之变局”,也没法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甲午之后向西方寻求真理(包括通过日本作为中介来学习西方)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但他们在情感上和生活方式上(也包括鲁迅、胡适等人)对这个文化传统又有很强的眷恋,列文森认为这两者之间构成精神世界的紧张。您聚焦的是富强与价值之间的冲突,而列文森在这代人身上所观察到的是理性与情感的张力,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列文森是认为理性更强一些,情感更弱一点;您书中的“富强”与“价值”是用更加对等的两个观念来剖析当时的中西相遇及文明之冲突。
杨国强:列文森叙述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一种真实存在,通观而论,虽以严复那代人为典型而表现得比较分明,而其一脉相延则在后来并没有消失。但就这个题目本身来说,列文森的分析恐怕更多地立足于旁观的返视和整体的观照,把这些人看成是一种静态的被分析物,因此他所标示的理性和情感之分而为二,似乎是同时发生,又同时存在于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形成一种同时俱来的两头夹逼,其重心显然不在思想过程,而在思想状态。
我初读他的书,曾经非常折服,现在我对他仍然很佩服。但在读过康、梁、严复留下的已经出版的全部文字之后,我更相信把他们的思想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从而变化之中的过程,似乎更接近真实一点。这些人都起于19世纪末期的戊戌前后,而重读他们在那个时候倡导和恢张西学的炎炎大言,则所见俱呈一派深信和羡慕。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是一面之词,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文章和严复发表在《直报》、《国闻报》上的文章也是一面之词,其各自表达里都看不到理性和情感之间的不相容和紧张。以此作对比,真正的变化其实开始于20世纪初头的十年新政,又彰显于民国前期的乱世混沌里。分别而论,康有为因亡命海外而作汗漫游,“足迹所至遍十三国”,遂以此日之眼见目睹,校正往日的传闻之知,“率以为莫吾中国若也”。之后是西国既非天上世界,则深信羡慕随之俱灭。而梁启超和严复之后来不同于以前,则更多地是因为十年新政中灌入的西学和引来的西法,一旦化为人间景象,其横决佚荡和冲突厮斗往往既非他们当初之所能预想,又非他们此日之所能接受。
就思想的逻辑起点而言,这些人在19世纪末年本是为求富强而倡西学,但在20世纪的中国,却是西潮澎湃之下富强犹不可见,而构成五千年中国文化内核的人伦已为横决佚荡和冲突厮斗所伤而体无完肤。这种后来被称为价值的东西一经撼动,导致的已是人在其中,而心灵全无宁日。数千年历史文化形成的人伦已经化为习俗和融为习俗,它们与中国人的人生相伴始终,但又因太过熟悉而无须思索,遂在与之浑然一体的同时却常常相忘于浑然一体之中。因此,当这一代人力倡西学之日,大半不会想到中国社会的这一面,直到西潮冲击人伦,才会痛切地看到这一面之须臾不可或缺。就像平常你不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留意自己的心脏,总是心脏出了毛病才会感觉到它的真实存在和非常重要。有此不可或缺,而后是他们对西学之行于中国由深信到疑虑,由疑虑到排拒。比较而论,在这种翻江倒海的心路历程里,梁启超因游移于两头之间而受到的痛苦最多,而严复因其先倡的西学对中国人伦伤害之深而受的痛苦最多。但就其人生走向而言,两者在其晚年都更明显地回向了传统。
因此,列文森用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抉示了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真实矛盾。但他所作的静态分析,又无从容纳其中不同个体在变化之中,从而是动态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各不相同的具体性。而且深而论之,就当日初倡西学的人物群里多数并不真知西学和深知西学而言,则用理性一词总括他们对西学的态度显然是过于宽泛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其中的盲目一面。就人类的认识而言,盲目性是不能归之于理性的。同样,若单以情感一词概括这些人之不能脱出传统,亦稍嫌过狭。他们从初期力倡西学的立场朝后退,相当一部分原因出自于由原本漠视中西之间历史文化的区别,到屡挫之后不得不正视中西之间历史文化的区别,从而是由原本用太过简约的思维来对付一个复杂的问题,转变为用复杂思维应对复杂问题,其中显然内含着困而知之的所得。因此在更加激进的后起者眼中,他们的变化是一种“反动”,而就其自身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实现于老年对于青年的自我否定中的思想成熟。是以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有些用质疑的方式表达的见解,至今读来仍能感到深刻而引人长思久想。

至于你所提到的鲁迅,恐怕又属另一种类型。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议论其实非常接近于他的老师章太炎,面对西学有一种不肯盲从的意态。他在1908年所作的《破恶声论》里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又说:“若夫自谓言之尤光大者,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稍耳物质之说,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曰:‘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秘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傎乎。”他所抵拒的种种社会现象显然都是以西学为源头的。而尤其使他意不能平的,是科学主义的泛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淹没。
但时隔八九年,当他汇入新文化潮流之后则翻然大变而成为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终其一生未尝再有彷徨游移。其中成为鲜明对比而尤足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里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论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所以“讲科学”应取其能“发议论”。这些话说明,他之所以借重科学,要义不在科学本身,而是要用来作为打倒传统的利器。比之当年他所视为“不亦傎乎”的泛科学主义,显然更加泛科学主义。因此把他列入理性与情感矛盾的一类里,至少不能算是非常典型的。而对于我来说,更想弄明白的是清末的鲁迅何以转变为民初的鲁迅,但其间的思想演化轨迹至今还找不到能够具体反映其个人经验,而又非常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可供思索。
中西文明的相遇
唐小兵: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比较关心两点,第一是谈到东西两种文明在晚清相遇的时候,一个是中国文明具有历史惯性的优越感,以古老的夷夏之辨铸就士大夫阶级的心理防线,另一个是西方文明挟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的技术、理性上的强烈优越感介入中国,这两种优越感之间形成尖锐对峙,然后历尽冲突又重组的过程。按照许纪霖教授前些年的一个观察,其实西方文明也有两张面孔——有富强的和文明的面孔,中国的文明也既有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也有法家式追求富国强兵的面向,为什么当它们相遇的时候正好所激发的是隐含在文明体系里面带有极端性的一种价值,而内省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没有被激发出来并相互刺激?另外,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强的预设——历史中的个人或群体是不能摆脱自己的历史经验来深度认识或对待一种外来的异质文明的,但是我在想 ,人除了经验主义之外,还是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去认知不一样的事物,那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有内化出这样一种思想养分来认识异质的存在?这是不是像您在《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长文中所说的,中国的科举体制所创造出的一群士大夫是反学问的——反感甚至排斥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探索,更多地依托个体或群体的历史经验?
杨国强:中西文明在近代相遇,先是以物力为比较而由战争作前导,后是以文化分优劣而一方灌入一方。以这两面所构成的定势作度量,则中国人与西方世界大规模的交冲起端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便已处在前代历史留下的两种无从自主的劣境之中。以时运而言,在18世纪的盛世过去之后,继起的19世纪已在“四海变秋气”里走入衰世。然则以衰世中国与工业革命之后正当如日中天之际的欧西作物力和暴力之比,留给中国人的便不能不是步步颠蹶和创巨痛深。后来称之为沉沦的过程正是由此为开端的。
而比时运更深一层地影响了后来的,则是清代的学术。清学之自成一局,起于对明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否定。其此长彼消之间未必没有学术推演的内在逻辑。但时至乾嘉,这种推演已一变而为力张汉学而排抵宋学,并沿同一种理路而疏离了中国文化中的史学传统。前者是用知识之学反对义理之学,后者是用知识之学盖没“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本义。而由此浸为一代学风,则使19世纪中叶之后处中西交冲之下的中国人越到后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因义理的稀薄,遂身处剧变之世而内里缺乏足以自立的本原;又因史学不振,遂由不能切知过去的中国而不能真知当下的中国。因此,当本在乾嘉余风熏染之中的一群一群士人既为世变所迫,又为世变所牵,而直接以清学接入西学之日,随之而来的,便不能不一路张皇,一路奋力,一路挫折:因内无自立的大本大原而只能跟着西人走,又因不能深知由历史化育的国情而轻信西学可以全变中国。
近人论史,常常痛责中国人的保守,其实真能保守,须内有可守。而衡之以历史事实,自19世纪中叶算起的一百一十年里,前期之保守大半出自懵懂和虚骄,迨懵懂虚骄一经打破,之后的时趋便对灌入的西潮由拒而转为迎,并曾在节节高涨中催化出“以西学为神圣,视西人如帝天”的另一种极端。与极端的保守不肯应时而变相比,后一种极端则弊在丧失自我。比较而言,后者对近代中国的总体影响其实更大。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常常会与西化相交缠,或径直被称作西化,其历史中的来路盖在乎此。若以这段历史的背景省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以及中华文化学术之复兴,“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则不能不说中国人在义理之学式微的时代里徒以训诂之学与西人西学相迎于天翻地覆之日,实是因学术演变造成的一种历史的不幸。
至于你所说的内省,同样与这种学术的分异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义理之学不能不讲内省,而训诂之学则无涉于内省。因此,近代中国最困难的转折实际上发生在洋务运动的起端,而与这种转折相对应的,便是曾国藩那一代人处中西之间审量彼己的内省。但以学术源流而论,其间的人物大半并不出自乾嘉之学那一脉,而更近于清代仅存的宋学的绪余。与他们比,后起的变法更多自我批判,但自我批判意在脱胎换骨,就内涵和外延两面作论说,实际上都已越出了内省的本义。

最后讲一讲你所说的历史经验。从一面来说,经验是成功的积累,也是失败的积累。前人真正能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这两种东西。因此,人类的文化延续,本质上就是人类历史经验的延续。而经验之能够不断地延续,实际上又同时在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可靠。从另一面来说,人类认识过程的天然限度,是面对未知的对象,一开始只能依靠已知的知识为尺度,所以一开头总是会引用已有的经验相推度。你所说的“创造性的思想”,若一层一层追问下去,最终也一定会有与之相应的经验为之托底的,否则这种思想全无来路,又何以使创造性成为真实性?
对于那一段历史来说,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创造性”,而在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里曾经包含着足够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但逼来的西方世界却出自这种历史经验之外。两头构成的矛盾是:旧有的经验既已不足以对付经验之外的西方人,则中国人不能不走出自己的历史经验;而数千年历史经验中累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又使久在其间的中国人不容易脱出历史的惯性,去切近地正视、审视和认知这种虽不能为历史经验所容纳,却自有一副本来面目的东西。我在前面所说的近代中国最困难的转折实际上发生在洋务运动的起端,正是指为洋务开先的一代人,在自己的正视、审知和认识之后,用借西法以图自强的论说和践行,促成了一个与历史经验相伴相守的民族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历史经验。以一个民族为主体探究其认识过程,这种转折的困难程度其实比后来的变法和革命更大。而就这些人大半都由科举得功名而言,则你所引的科举制度内含的知识限度一节,对于这些人实际上并未产生影响。因为科场限度制约的是科场,而科场之外仍然有不能为科场所限的文化空间。
近代知识人为何多变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一文中,您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个案来看问题,谈他们在民国时候的一种回归和对传统的反思。您怎么评价梁启超的善变,思想上或政治上的善变?而且,按照钱穆的说法,从清末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学风是一条下行线,无论怎么看那些士大夫的品质都是有问题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杨国强: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梁启超以流质多变而自塑了一种个人形象。但泛而论之,则应当说,在那一段历里,多变曾是一种常态。读当时人的文集,论旨的前与后互歧,同一个问题的此一时与彼一时相悖,都属常见和熟见的事。而梁启超之所以以其多变而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他确实变得更多,变得更快,变得更主动;二是因为他既以言论得大名,其一变再变又皆辛辛苦苦、孜孜矻矻地付诸文字而张布于言论界,致使其多变既为天下所共睹,遂为天下所共晓。

那个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很多,而可以引来为这些问题作诠释和供阐发的东西洋学理同样很多,处于两种很多之间,实际上是处于目迷五色之间。一面是引入的学理此长彼消,而来去匆匆之间留下的则是种种扞格;一面是作为受众的中国人在此长彼消和来去匆匆里一路跟随,蹑而从之。而后是自清末开始到民国前期,世间众生之新我不同于旧我,其变化的程度常与他们身在时潮之中的投入程度成正比。是以在那个时代里,多变在外观上虽然出自个人自主的选择,而骨子里则大半都是随时潮而趋走的被动、盲目和不知其所以然。
但与多数之随时潮而趋走相比,梁启超是一个营造时潮和导引时潮的人,因此,与多数的被动相比,梁启超的多变是主动的;与多数的不知其所以然相比,梁启超的多变又是真诚的。由于既是主动的,又是真诚的,所以每一段变化都会在他个人的思想历史中留下明显的痕迹,而他所曾经据有的执言论界牛耳的地位,则常常会使这种个人思想历史中的痕迹同时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痕迹。也由于既是主动的,又是真诚的,梁启超比多数人更自觉地意识到,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否定。他所说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则直白地说明:这种否定的实质尤其在于自我否定。因此,他个人的思想历史中又留下了重重矛盾和牴牾,并富有代表性地折射了近代中国那一段思想历史中的矛盾和牴牾。
就其多变所反映的历史内容而言,梁启超是从那个多变的时代中产生出来的人,是由那个多变的时代造就而成的人。这个时代需要有人以思想回应和写照其千变万化,也一定会催生出以思想回应和写照其千变万化的人。所以梁启超之所以为梁启超,其实是历史过程里的一种典型。然而就个人一面而言,以梁启超的多变对比康有为的一变之后不肯再变和章太炎的小处间或有变大处守定不变,则又具见同在一个时代之中,也会有人之不同各如其面。而后便不能不论及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才识情性。梁启超是天赋很高的聪明人,康有为和章太炎也是天赋很高的聪明人。但康和章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是他们很早就形成了自己整体上的学术构架和价值立场,并由两者合为一种内以自守的东西。因此,置身于一个多变的时代,他们能够以自己之所守作应对,便显出了不会轻易跟着走的定力。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由此立论,可以说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天赋与聪明更多地归趋于内在的一路。而引此二者以相对照,显然是梁启超的天赋和聪明从一开始就发煌于外向一途。这种外向的聪明使他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新知,并不止不息地吸取新知。在一个新知由少到多,又各以其一面之理纷呈地汇为一时之强音的社会里,他曾因之而得大名。然而多变于新知之间,本义上已是一种不停的追逐,由此所获得的东西,既不会有太多的深刻性,也不会筑成内在的稳固性,于是思想便只能常在既清且浅的流质状态之中。末期梁启超回归学术,以渐见稳固性而别开气象,但天不假年,未久便遽而谢世,这是很可惜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举康有为、章太炎与梁启超相类比,比较的不是他们各自的思想里所含有的真理在数量上的多少,而是陈述个性的不同最终可能会导致的思想路径、思想方法和思想程度的不同。
至于你所提到的晚清以来士大夫的品质,说起来还要更加复杂一点。如果就个人而论,后来的人物之间还是有高低可分的,例如刘坤一的君子人格就比张之洞更多一点,梁启超的君子人格就比康有为更多一点,汤寿潜的君子人格就比张謇更多一点;再往后说,则黄兴的君子人格又比陈其美更多一点。但总体而论,后起的新人物在德性一面确乎常常逊于前一代人物。即使是老革命党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里叙述清末史事,也有过新人物人品不如旧人物之议,其实他自己当日也在新人物之列。
若事后追溯这种变化的起因,我所能看到的大约有二点。一是西学的传入使原本一统的价值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崩离析。于是而有新道德、旧道德、公德、私德之辨,结果是本来人人都明白的东西,在这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论述里日趋虚幻而陌生,道德原有的束缚力也随之弛脱。先倡此说的梁启超后来自己也明白道德本无可分新旧和无须分新旧,但经此搅动,人心已在迷离莫辨之中,而后是一统的道德很容易地变成了各是其是的道德。时人谓之“公德之利益未见,而私德之藩篱先破”。二是清议在这个过程里的衰落。二千年中国士大夫功名得自朝廷,而德性则靠清议的制裁和管束来成全。而清议之所以能够制裁和管束,全在于清议出自公论。每个人都是评论别人的人,每个人又是被别人评论的人。中国用报刊造言论,而后有所谓舆论界。就字义来说,舆论也是一种公论,但与清议之不可操弄相比,舆论又具有明显的可操弄性,所以舆论所带来的公论的混沌,最终一定会使同属公论的清议不复再能拥有其评断是非和管束人心的力量。而人无内在的管束便容易走向轶荡。

冯志阳(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您在历史研究上似乎有一个自我的感觉。1949年之后,像革命史观、现代史观基本上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但是我觉得您从一开始完全超越了这两个范式的窠臼,您三十年前的文章,现在读来还是很有生命力,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类似“义理”、“民本”思想等久已被遗忘的儒学价值观渗透在其中。整体感觉您的史学解释的方法是用内圣外王这种比较原典的东西来看近代的人物和思想,包括那些别具一格的词语、概念背后是一种价值理念和体系。儒学的精神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历史,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需要理解儒学,您在这些文章中对价值观的引入只是为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去探究历史的原貌,通古今之变?还是像韩愈和司马光那样“文以载道”,以史载道,以史布道?之所以会有这个疑问,是觉得您在文章中对与儒学价值观更为契合的人物与现象有着更多的同情、理解,乃至认同。
杨国强:你说得那么有条有理,太过抬举。我自己有时候回头返视,看到的却大半是一路走来的七颠八倒和困而后知。这个过程除了心态上的既苦且累之外,还有常年相伴的那种静如止水,青草悄然茁长的落寞和沉寂,古人说的生涯淡泊,庶几乎近之。而这种落寞、沉寂和淡泊所给予的造就,便是使人可以自主地思考和漫无边际地思考。所以落寞、沉寂、淡泊又并非全然都是无情无趣的东西。
从时间上算,我们这一辈人是在八十年代先后进入学术界的。回想那个时候的人物、思想、议论以及种种大题目和小题目,至今还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可以大约言之的,一是理想主义,二是进步主义,三是对于现代化的向往。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三种东西之能够吸引人心,其间的一大半原因是这三种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抽象的。因为抽象,所以有足够的余地可以各作想象。虽说彼时我们犹在学界的边沿,但我以读史为业的人生过程则非常明白地是在八十年代思想潮流的影响之下开始的。
史学面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从而是既定不变的事实,然而后人读史,又一代有一代的视角和视野,从而一代有一代的关注、勾连、理解和解释。同一段历史之能够一遍一遍地写和应当一遍一遍地写,其理由都在于此。与八十年代的知识人以其对现代化的各自向往化为合群的呼喊相比,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并且越走越远地进入了现代化的实际过程。这个过程使我们直观地看到种种构成了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并因之而比八十年代更切近地目睹了现代化。然而在这个大幅度增长和发展的过程里,与增长和发展俱来的,还有社会的深度搅动。而与后一面相因果的,是物利盛涨之下,价值在游离中脱落;稳定因竞逐而解体,精神随意义的远去而猥琐,以及当下在人心中与过去的断裂和当下在人心中与未来的断裂。这些都是八十年代所向往的现代化里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它们与增长和发展一同出现在九十年代之后,既使曾经抽象的现代化变得越来越具体,又使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化正显现为一种兼具多层内容、多面意义、多重矛盾的历史过程。因此,与实际过程中正在节节铺展的现代化成为一种对比的,是作为认识对象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越来越纷争多端而难以走向统一。虽说与八十年代相比,我们更切近地目睹了现代化,但能够像八十年代那样自信已经真懂现代化和全懂现代化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我之所以不嫌聒噪地追叙三十多年里的这种思想迁移,一是因为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形成的问题已非常不同于八十年代,而一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则不会不导引一代人的眼界和思维,并牵之以入各自的专业之中。二是因为经此七颠八倒,我已很难再相信用抽象的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可以统括地和完全地解释作为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的现代化。最终是两者都影响和改变了我读史的视野和视角、重心和理路,并因此而对曾经被进步主义过滤掉的那一面多了一点自觉的关注。历史虽然是一种已经远去的往事,但若以社会转型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代一代中国人共同面对的主题,则对于今天中国正在实现的现代化而言,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同一个过程里的一段前史,从而我们此日所面对的问题,常常也是前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因此后人审视这一百一十年里的人物、思想、史事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相似的东西,古今同慨的东西和有触于胸中之所积的东西。而沿波讨源,又会由一百一十年牵及二千年。在这种感知和感应里,被时间和空间隔开的历史往往会变得很近。
把过去作为研究的对象,历史无疑是一种客体;但就过去仍然在影响现在而言,历史又不纯然是一种客体。所以,你提到的“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讲得非常明白的题目。在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里,有一类是具体的,因此是可以实证的。而由这种用考辨重建史实以重建真相所得到的答案,不仅是确定的,并且常常也是唯一的。还有一类则因其古老而又常新,实际上成为每一代人都不能不回应与回答的问题。然而这一类问题大半深涉义理,又在不同的世局中理一分殊,是以其间内含的道理虽一以贯之,而每一代人的回答都不会成为最终的答案和唯一的答案。因此每一代人在自己作了回应之后,又不能不把同样的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世局中寻找自己的回应。
举例来说,二千多年里,中国人的政治、道德、社会都与义利之辨相交缠,遂使一朝一朝的中国人都须从政治、道德、社会的虬结之中去回应义利之辨。而一段一段地看,则清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同于宋人的义利之辨;若今人有心关注当世的义利之辨,其思考和回应也一定会不同于清人。这一类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但又因其实际上成为每一代人的问题而构成了一种漫长的和不间断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用同样的问题把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以时序为先后串联起来,并且在同样的问题里汇积了每一代人身处于不同的世局之中,而各自都倾力于寻求同一种东西的心路和理路。虽说与历史中的世局、世相、情节、细节相比较,由这一类问题在串接和汇积中形成的历史过程缺乏十足的直观具体性,但世局、世相、情节、细节的起伏舛错却大半直接或间接地与之内相关联。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历史中更多形而上,也更具深沉性的东西。因此后人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由阅读而理解,由理解而解释,从而在各成片断的事实中看出连贯的意义,则不能不顾及和认识这一类不同于具体问题,而又曾是每一代人都身在其中的问题。
然而由事实进入意义,实际上是由简单走入了复杂,并因此而很容易为名目各异的种种“史观”增添麻烦。一方面,片断的事实连贯为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同时又一定会呈现出历史的多重内容和多面意义,而今日被称为“范式”的东西大半以构架厘然、条理分明见长,但厘然和分明常常是以舍弃一部分不能纳入构架和条理的内容为前提的。所以厘然和分明都不大能对应历史本相中的多重和多面。另一方面,以事实为对象,历史只能一段一段地研究,但着眼于历史中的意义,则每一段历史都由前一段历史而来,并长在前一段历史留下的规定性之中,因此读史需要朝前追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在这种延长了的时间过程里,立足于短时段的观照与立足于长时段的观照未必总能互相对应,是以处在两种观照之间,历史演化中的事实性、合理性、道德性和真理性,遂并不尽能层层迭合而归于一致。这种不相对应和不能一致各有自己的理据,因此,他们最终反映的是历史内涵中的错杂和多端,以及历史内涵本身的丰富和广袤。而对于说明历史和理解历史来说,则一方面,错杂、多端和丰富、广袤都太过无边无际,既不是一个人能够穷尽的,也不是一代人能够穷尽的。由此形成的技止乎此,是认识对象对于认识主体的限制。另一方面,读史而用心于探究历史中的意义,是因为历史至今仍然在影响现在。但每一代人意中的历史意义,大半又是在他们所处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主要关怀的引导之下和反照之下界定的。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眼光,遂使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于历史意义特定的关注所系和重心所在。由此形成的视野有定,则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限制。然则身在两重限制之下,每一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有限度的。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史观,不同的范式之所以同时存在而又相互立异,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限度,而限度又很容易演变为界限。
由你的问题引出了那么多话,绕来绕去,主要是想说明三十年史学生涯之后,我对史学本身的一点领悟。因为这一点领悟,所以,第一,我用文字所表达的,是我在通过阅读进入历史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感受和思考,就我个人而言,这些都是真实的,除此之外,其实没有更多的深意。但实际存在的历史转化为文字表述中的历史,又只能通过个体的思想劳动来实现。因此客观的内容常常会留下主观的印记,于是而有显现于文字之中的不同个体的不同个性。在这一点上,我同其他人一样,既有自己的视角、视野,也有自己的限度,而由此形成的个性,在供人阅读评判的时候便可能引出种种联想和推测,然而这些都不在我预先设定之中,所以往往出乎我的意料。第二,历史学中的体系和范式都各有理论,从而各有方法。但读史既久,我更相信史无常法。因此,我对三十年来的各种体系和范式虽深抱敬意,却宁肯远看以示仰慕,而不敢以身自附,在他人脚下盘旋。以我有限的能力,遂只能越过方法以直面历史,并力求用历史本身解释历史。至于你所提到的“别具一格的词汇、概念”,也不过是有感于现代汉语与古人世界之间的隔阂,而不能不多下功夫于常用词汇之外,目的不过是更能达意而已。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也是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