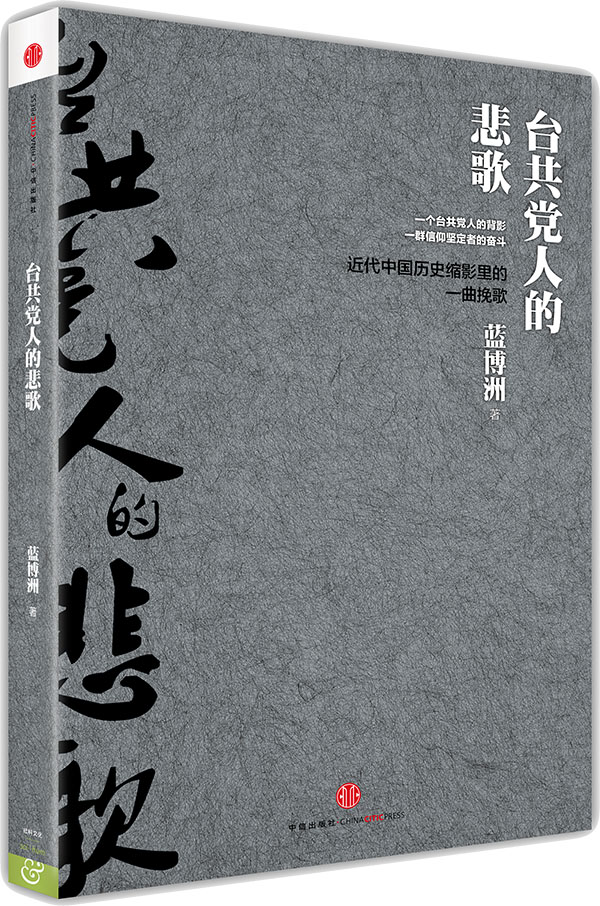汪晖对话蓝博洲:反驳“台独”史观,让台湾民众多了解中共
【编者按】
1945年日本殖民地台湾回归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组织地下党活动,与国民党展开长达八年的斗争。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共产党机构曾组织过暴力起义、武装割据等活动,但因实力悬殊,抵抗数年后终被血洗。一部分台共党人或投降、或叛党,但领导人之一张志忠夫妇却于1954年从容赴死。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的新书《台共党人的悲歌》即以张志忠夫妇为主角,展开描述了那个时代里怀有信仰的台共党人群像,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段缩影。近日,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简体中文版,9月14日,新书发布会暨“寻找失落的台湾历史记忆”座谈会邀请了台盟中央官员、著名历史学者、老台胞、台湾文学批评家等人致辞并发言。经授权,澎湃新闻特摘取与会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和作者蓝博洲本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汪晖:首先我祝贺蓝博洲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几个月前,蓝博洲先生和我的朋友让我来写一个序言,我其实是非常惶恐的,因为台湾去过多次,但是谈不上理解。因为从甲午战争到两岸分治的格局形成,两个大的中间有日据时期,发生太多的事情了,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不仅是在这个区域,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所以怎么去把握这段历史?我觉得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读蓝博洲先生这本书的时候十分感动,感动于当年的革命者,这样献出自己的性命,为了民族的解放完全忘了自己,这种精神在今天实在地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们可以敬佩,但是你要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这样做,他们身上的精神,我们应当礼赞,但是真正想进入他们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斗争生活,既要有信念还要有政治上的了解,这样的过程不是一个今天那么多人容易接近和理解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第二个感动,是感动于蓝博洲先生,从他早期的写作开始,前后将近30年了,一直在努力发掘这样的历史。我自己在序言里面也说过,他似乎用他的写作把自己嵌入到这个历史的现存里头,他身上有一个使命感,要连接起先辈的斗争和今天这个时代。这当然不止蓝博洲一个人,他们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由于时代发生重大的变化,就特别需要有人,不仅是叙述,而且是身体力行地让你感觉到这个历史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就还能生长出新的东西来,如果中断了再去接,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台湾的特殊的历史命运,连接传统的努力,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钦佩。
第三,我觉得读完他的这些书和他的其他著作,有很多感慨。我自己做一点思想史、文学史方面的研究,深知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实在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研究,会发现研究十九世纪,或者更前,大家的兴趣很大,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尤其是跟革命相关的历史,其实是非常难的,不仅是史实方面的问题,而且是逐渐地失去了对这个历史时代的脉络、气质和精神的把握,这个动力越来越稀薄。历史发生变化了,今天两岸关系也发生变化了,因为统一的问题,统独的斗争,敌我的关系,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产生出来的变化的敌我关系到今天又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所以这样一个变化的条件下,怎么理解这个历史传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来说,要理解犹为困难。我们怎么发掘和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这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所发生的斗争,这几代人的命运?从台湾的角度,我觉得蓝博洲先生的工作给了大陆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契机,一个重新从一个特殊角度去看待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角度。今天,我们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对于毛泽东的争论都是巨大的,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在大陆流行文化中,“民国热”非常盛行,用这样语境来阅读蓝博洲的作品,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们一些震动,让我们重新进入到历史里面,去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乃至理解我们生存状态。过去,我们老师一辈的,都早已经提出“告别革命”这种说法了。告别革命,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状况,因为在今天不太可能再回到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大概也不大会有人这样去想问题。但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不等同于对革命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传统的否定,如果把这个历史传统否定了,我们现在的中国认同,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源泉和历史的地基都会被动摇,这是今天这个中国社会面临的非常巨大的问题。
更不要说,我们的双战构造,也就是内战、冷战的构造,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重新巩固。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发掘这一段历史,不但是对先烈的一个纪念和致敬,也是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今天到底如何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思考这个突破双战构造的方式的可能性,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启迪。我也觉得特别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当中,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顺便说几句,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叙述里面,台湾的现代史,台湾现代史,台湾的文学,可以说是被提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门类放在这样研究。比如我们教现代中国文学,或者教现代中国思想,并未将台湾内置于叙述,它实际上是中断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叙述现代中国史、现代中国思想史或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台湾问题是放在另外一个方向的,由一些特殊的专家研究,不是在我们的基本的教科书的或者是我们教学的基础性的框架里面,这个状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不改变,就等同于我们的知识状况服从于双战构造的状况。我们如果不能找到一个方式来突破这个冷战和内战给我们造成的隔绝,在思想上、知识上、情感上作出突破,那我觉得对年轻一代人而言,这个机会更失去了。因为日常生活的实际的确是存在的,在今天需要有一点紧迫感,在中国大陆需要有这个紧迫感。我知道很多台湾的朋友有这个紧迫感,但是在中国大陆有紧迫感的人很少,我实话实说,没有这样的紧迫感,是对于问题缺少一个尖锐的意识。所以我很高兴蓝博洲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我也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带动更多台湾朋友的著作在大陆出版,给我们一个机会,也使得大陆的学者和写作人能够跟上,把这些工作重新接续下去。

你说接受这样教育的一代人,他能不反共、他能不恐怖吗?不可能。所以我自己1979年在学校任职的时候,整个校园是一片肃杀的。然后过了一个学期才慢慢平常。当时大家都支持民进党。参与党外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谣传说,好多年以前,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人,刚开始不敢说,我们只听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很隐讳地讲,国民党在台湾杀了很多台湾人。慢慢地才知道,那个符号出来了,“二·二八”。
我15岁立志要当小说家。搞文学的人要关心社会,要了解自己土地的历史,所以就试着理解这些传说中的一些历史,可是真的是找不到答案。我经常想,两岸的问题,身份认同的问题,该怎么看?比如今年所谓“太阳花”的闹剧,就是说你怎么让台湾的年轻人认同,认同中国。希望两岸统一?我觉得很难。用什么来吸引他们?他们是活在一个“反共”社会的年轻人,他祖父、父母都“反共”,他不了解后就“反共”,他尤其受这一代人的影响,喝去中国化的奶水长大的,根本没有中国心,中国情,我们这一代老讲“反攻”教育,但我们还是有中国情、中国心的,虽然要“反攻”,但都是中国。但“台独”就是不要长江黄河。你只要回想受教育史就知道,你的中国心、中国情还在。部分新一代青年不是这样的,他已经没有中国心、中国情,他也不一定反共,他也愿意来中国大陆,他觉得他是出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愿意交流,愿意参加夏令营,但他没有认同。他也不了解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长征的共产党?他怎么知道1921年的共产党?他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首先要在宣传上让台湾民众多方面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它怎么走过来的,这个还是要想办法用各种方式让台湾了解,了解了以后,你才不会没有道理地恐共。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到底跟台湾,跟台湾人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有很多东西要讲,而且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台湾人民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和建设,台湾人是参与的,不是区隔的。你让台湾民众了解了以后,台湾民众可能才会有所认同,要不然我觉得前景是无解的,让人悲观。光是经济让利,是争取不到民心的,民众不了解,如果让台湾民众知道更多的相关历史,那你就可以把被颠倒的历史就颠倒过来。
我接着就说,我的《台共党人的悲歌》,还有其他的一些写作,它的意义是在这里,它对“台独”历史的论述有一种反驳,比如,“台独”说“二·二八”以后台湾人开始搞独立运动,这是谎言。“台独”是土改以后才开始有的。我们要有更多的历史事实,去反驳他这种被他们收归过去的历史解释权,要不然就很难。“台独”叙述的历史虽然是假的,但是影响着老百姓和媒体。
到现在我们搞白色恐怖的纪念活动,媒体也说“二·二八”,在台湾“二·二八”就等于是“台独”。因为很多人本身就同情“台独”派,所以我的书在台湾卖得越来越不好,他们不理解这种情结。
总之,台共的历史前面讲了很多。你如果不理解、不处理会流失更多的东西,包括地下党历史的家史,这个是让人家很痛心的,但是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父亲、母亲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不知道他父亲是共产党,他会说怎么可能是?如果烈士的家属都反对烈士的理想,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最大的悲哀,我不指望我的书能影响一代大众,但最起码要影响这些烈士的家属,如果这个都做不到,那我就不晓得我们要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怎么谈统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