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华兹华斯的前后之变与……时代悲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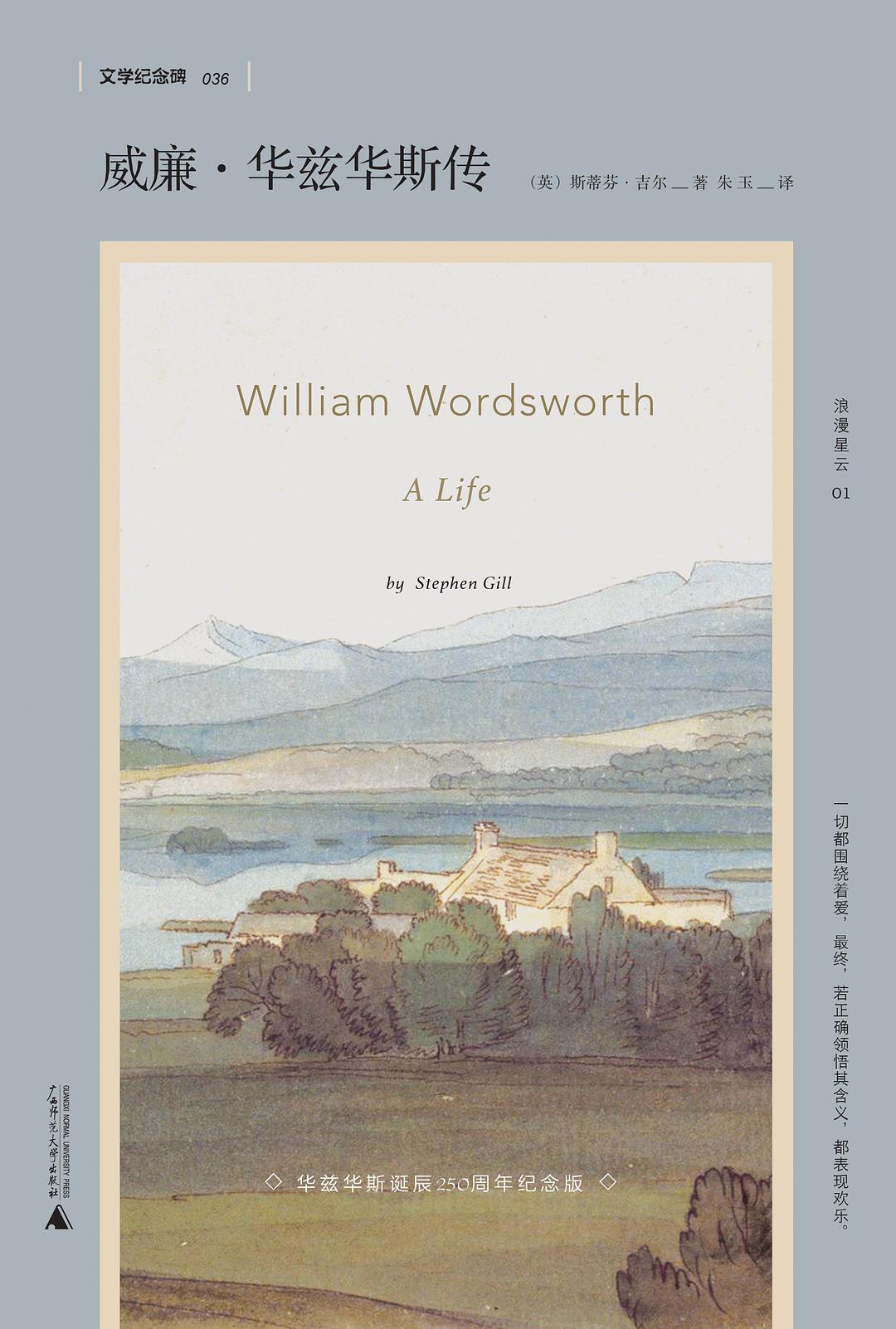
《威廉·华兹华斯传》,[英]斯蒂芬·吉尔著,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912页,186.00元
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过去我和我的同代人最熟悉的恐怕是雪莱的“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可能还是通过《青春之歌》读来的)。原以为这是喝“狼奶”的结果,后来读玛里琳·巴特勒的《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作者说“我们想到浪漫派时,我们想的是雪莱和拜伦。或许,在20世纪后半叶比在19世纪更容易相信浪漫主义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梅、陆建德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才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最早认识的华兹华斯诗歌不是他的“孤独的云”,不是他在湖畔吟诵的自然风光,而是他的《序曲》中回忆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句:“能有这样一个黎明是幸福的,何况年轻,简直天赐!”忘记这是谁译的,至今我还是最喜欢这一译法。据说英国疫情期间的宣传车要行人保持距离,于是反复播放华兹华斯的诗句“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华兹华斯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幸福的、年轻的黎明。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学生乔纳森·科特来到伯克利大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波文化和政治觉醒的中心,他很自然就感受到两个世纪前威廉·华兹华斯回忆亲历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心情,想到了那个幸福的黎明。他还马上从华兹华斯想到了当时流行的鲍勃·迪伦:“……无论你走到哪里,就像鲍勃·迪伦在《郁结如麻》中唱的那样:‘夜晚的咖啡馆传来音乐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当时他无法想象的是,在五十多年之后诺奖委员会给迪伦的颁奖词有这么一句:“他重新赋予诗歌以高昂的姿态,这是自浪漫主义时代之后便已失去的风格。”虽然这里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高昂姿态可能指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二代传人,但是科特从华兹华斯到鲍勃·迪伦的联想还是有道理的。黑塞在给一个年轻的《梦系青春》读者的信中说,“没有革命的经历是形成不了人的。”是啊,如果没有过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黎明与青春,成长还有什么意义呢?
斯蒂芬·吉尔的《威廉·华兹华斯传》(William Wordsworth:A Life,2020;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丛书,2020年11月)记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一生,从亲眼见证和拥抱法国大革命的热血诗人到维多利亚女王亲授的桂冠诗人,也描述了他和家人、朋友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历史环境,同时也探讨了人生际遇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诗歌与批评家和读者的关系。该书初版于1989年,第二版是献给华兹华斯诞辰两百五十周年的礼物,出版于2020年4月。新版补充了三十多年来发现的新材料和吸收了学术界的新成果,例如尼古拉斯·罗、肯尼斯·约翰斯顿和约翰·沃森等学者的研究,全书的注释、索引、参考书目和附录估计或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根据第二版翻译的中译本能在同年出版,这是很令人惊讶的速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权威的华兹华斯标准传记,是一部“洞烛幽微”“充满人性”的作品。
斯蒂芬·吉尔在2020年5月写的“中文版序”中开头就说,华兹华斯的作品对他有着持久的意义,多年来对其作品的价值笃信不移。但是这意义、价值究竟是什么?以及什么是“这背后的原因”?他在这里没有正面展开论述,只是马上谈到十九岁的华兹华斯如何“怀着一位理想青年的全部热诚拥抱初期的法国大革命”,还有就是此后几年法国大革命的权力斗争、内战、流血和大屠杀的演变迫使许多和华兹华斯一样的理想青年重新评估他们的信念和希望,以及这种重估引起的痛苦与挣扎。这篇“中文版序”似乎有点针对性。关于华兹华斯早年与晚年的比较,作者在“序”就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大多数读者可能都有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批评共识,认为华兹华斯在四十岁之前写完了他最好的诗歌。本传记无意推翻这个判断。但在尊重‘伟大十年’的成就时,本书也力求呈现暮年华兹华斯的魅力和意义,这一时期往往被当作‘衰落期’而为人忽视。古稀之年,华兹华斯登上海芙琳峰,写下一首精美的十四行诗。那个华兹华斯在本书中非常重要。”应该注意的是,吉尔在这里的前后比较视角是诗歌创作的成就、魅力和意义,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前后革命时期的华兹华斯——则没有提及。“本传记的焦点依然是作为作家的华兹华斯。本书是一部传记,不是思想史,也不是对特定作品和思想时期的阐释。”(序)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作为诗人的华兹华斯毕竟无法与他的思想时期截然分隔,作者在传记中所提供的史料和相关论述仍然很有价值。
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第一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上的变化一直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议题。玛里琳·巴特勒谈到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的改变时,提出的问题是“这些本来有可能成为自由派的人是否也像那些德国人一样不自觉地表达了他们的社会对法国启蒙主义及其激进的政治后果的敌意?革命时代的伟大文学是否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种反应/反动的文学?”(同上书,第8页)也有中国学者在多年前撰写了专著,认为“我们在1792和1798年之间看到巨大的变化和反差。难道此中隐含着华氏‘反动倾向’的证据吗?难道这就是19世纪有的英国诗人、以前我国读者和现代英美学人从各种角度撰写社会分析、政治解读和文化批评类文章的温床吗?”(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很显然,“变”与“悲曲”都是大问题。作为普通读者,我感兴趣的是在华兹华斯的这面浪漫主义的镜子中看到时代的倒影,那个黎明与青春的最后悲曲。
1790年夏天华兹华斯在法国漫游,1791年11月到1792年12月他在法国居住。这时期他深受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感染,关注大革命的发展与问题,这是他的政治觉醒期。另外,大约在1791年12月华兹华斯爱上了法国姑娘安奈特·瓦隆,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但是他无法结婚和抚养女儿,只能在12月底回到英国。这是华兹华斯无法忘怀的岁月,其中的1792年则是更为关键的一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回忆,先是在1789年就怀着巨大的热诚欢呼那个年轻的黎明,当第一次跨海来到法国的时候,则是欢呼法兰西“正值最金色的时光”,颂扬人性在世间的再次诞生。真正的政治觉醒是第二次法国之行。1791年1月华兹华斯获得了剑桥的毕业文凭之后,一直以拖延来拒绝家族为他安排的神职生涯。他逗留在伦敦的日子显然受到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国政治氛围的感染,他大量阅读,旁听下院的辩论,通过认识一些人而思考意识形态问题与普通人生活的关系。“华兹华斯平生第一次萌生了政治意识,因为他交往的那些人都热切地关注某种理念和事业,并以各自的立场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怀有敌意。……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看到那意识形态的闪电预示着未来的风暴,他不会无动于衷。”(68-69页)他决定重返法国。
第二次来到法国,大革命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华兹华斯在布卢瓦认识的朋友米歇尔·博布伊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更重要的是在1805年写的《序曲》中,华兹华斯纪录了这样一个情景和对话:有一天他和博布伊在路上看到一位饱受饥饿摧残的少女,疲惫地拉着一头小母牛走着,双手一边不停地编织,“看到这景象,我的 / 朋友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是 / 为此而战。’此刻,我开始虔诚地 / 分享他的信念:一个幽灵 / 在四处游荡,势不可挡,绝除 / 如此赤贫指日可待……。”(75页)这是非常鲜活和强烈的感性和情感记录,是关于信念来自平凡生活的最好说明。但是吉尔也指出,华兹华斯客居整整一年法国,“他看到一个国家为摆脱权力、无知和欲望的专制,实现自由愿景,并维护已取得的进展不受外部侵犯而充满活力,因而越来越受感动。‘我的心献给人民,/我的爱属于他们。’这是他在《序曲》中的回忆,言语中流露出《景物素描》中那种宽泛而理想化的热情,其政治构想更多是来自书本而非经验。在法国,华兹华斯既无法获得革命政治的全面信息,又切断了来自英国的可靠消息来源,于是很可能坚信‘一个幽灵/在四处游荡,势不可挡’”。(103页)
华兹华斯于1792年10月29日从布卢瓦回到巴黎,直到12月底从巴黎回英国。1792年11月18日,一百多名在巴黎的英国人、美国人和爱尔兰人齐聚在怀特酒店(又名“英国人俱乐部”),欢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成就。他们中间有托马斯·潘恩、乔尔·巴洛、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罗伯特·迈瑞、大卫·威廉姆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伦敦政府和英国主流舆论始终对大革命极度仇视的时候,他们对大革命的成就怀有巨大的热情,并公开表示支持。吉尔没有提到华兹华斯是否也出席了这次有名的聚会,当然是因为没有史料记载的缘故。但是他指出,“无论华兹华斯遇见了谁、看到了什么,在巴黎的几个星期无疑加速了他的政治教育,他一年来的进展也有迹可循。……至于华兹华斯这段时期诗歌中的政治表述,我们也不能过于认真。”(78页)吉尔马上引述了华兹华斯在此期写的《景物素描》一诗的结尾中呼唤大地的重生,指出虽然评论家们认为这是华兹华斯写过的最富激情的诗文,结尾的高潮显然表明作者强烈反对君主制,但是他认为这些诗句仍属泛谈,“没有君主或政治家会从这种姿态中感到威胁”。同时他指出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华兹华斯返回英国三个月后写的《致兰达夫主教书》,它表明了作者的确非常了解法国近期的事件和问题的实质,而且有意识地运用了巴黎体验给他的优势。(79页)
华兹华斯回到英国之后发现局势变了。改良主义群体尽管要求不高,但依然被视为国家的威胁。潘恩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罪名是他在《人的权利》第二部分发表了煽动性诽谤言论。接着一大批出版商和报刊负责人因所谓的煽动性言论被判以重刑,政府显然决定要镇压国内的异见。曾经热情赞扬法国人民决心将自己与子孙后代从专制政权中解放出来的兰达夫主教理查德·沃特森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公开谴责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转而赞扬英国的强大、富饶、自由与幸福,并且庆幸英国政府的警醒和对持异见者的镇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华兹华斯立即写了《致兰达夫主教书》,激烈地谴责兰达夫主教。吉尔认为这确实是一篇非常激进的文献,华兹华斯不仅支持处决法国国王,而且还要荡平贵族,支持以暴力推翻专制。但是这封信没有公开发表,出版商可能因内容过于危险而拒绝出版,也有可能是华兹华斯自己出于谨慎而决定不发表。1793年7月,华兹华斯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独自跋涉,第二年完成了《索尔兹伯里平原》。在这首诗歌中他痛斥立法者使用的流放、恐怖、奴役、武力等手段,在他笔下的欲望、压迫、法律等抽象名词却是对应着他所熟知的具体现实,指向对合法社群成员的审判歪曲事实和对他们的判决荒诞不经。和《致兰达夫主教书》一样,这首诗在当时也并未公开发表。这时期的法国正是雅各宾恐怖统治的高涨,英国国内对激进主义活跃分子的镇压也日益加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关于此期的回忆是:“我很少有一晚安宁的睡眠,/ 因为眼前尽是恐怖的场景:/ 绝望、专制、死神的刑具,/ 在梦里,面对不公的法官,/ 我不停地争辩,声音嘶哑,/ 思绪如麻,一种背叛并且 / 被抛弃的感觉,击中我所知的 / 最神圣的地方:我的灵魂。”(114页)
吉尔认为,华兹华斯的思想转变大致发生在1796年。“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使大革命的光明希望蒙上阴影,然而他的倒台却没有使希望复明。华兹华斯依然坚信早期共和派的理念,并像所有激进分子一样,坚信战争本可避免。但是,当法国的扩张野心日益昭彰,特别是一七九六年拒绝英国的和平提议以及拿破仑意大利战役胜利后,他无法再相信战争的持续仅仅是皮特政府的阴谋,也不再认为在法国的一片骚乱之中,大革命的理想依然完好无损地存于某处。……一七九六年,华兹华斯没有清晰的信条可以宣布,一度的狂热分子已然失去信仰,甚至连相反的信仰都没有了。“(162页)但是他思想的转变并没有使他获得安全感。1797年8月,他被人告发身份可疑、与一群朋友关系可疑,内政部把他一家列为监控对象,第二年他在阿尔弗克斯顿租住的房子也被告知不能续期。这的确是“恐怖的岁月”,有学识的异见分子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因发表文章被判为煽动性诽谤和叛乱罪,有激进倾向的出版商约瑟夫·约翰逊被监禁了半年,“皮特政府的监视、恐吓和检举”极大地影响了他下一阶段的生活。
从政治行动中退出,不再相信激进政治可以促进普遍利益,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并非特例。葛德文撰文认为1797年春标志着法国大革命追随者的失败时刻,“一个个激进分子成为变节者,通过攻击曾经敬重的哲学家来标志他们的改宗。”吉尔认为葛德文指的是麦金托什、帕尔和马尔萨斯,“但他辛辣的分析或许也适用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 玛里琳·巴特勒认为,“华兹华斯可能是本能地屈从于一场争取人人平等的革命演变为专政这一现实,屈从于盛行的气氛。这现实和气氛在1800年左右使欧洲各地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变成隐退的或虔信宗教的人。也许他真正的独特之处是他向保守思潮屈服要比柯尔律治慢得多。他顽强地保有了很多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简朴、普遍性和对本质的人类经验的肯定这更使他与众不同,并引起怀疑。”(同前引书,108页)
另外,华兹华斯对待过去的态度与柯尔律治不同,后者与所有激进的朋友断绝往来,声称远离一切组织和活动——那些“国家政体肠子里的蛔虫”。他极力挣脱自己的过去,开始重写他的历史,在《文学生涯》中达到巅峰。华兹华斯却以不同的形式重估过去,本能地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寻找关联,以便证明生命的内在完整,因此不会拒绝从前的激进老朋友。1803年11月26日约翰·塞尔沃尔来拜访华兹华斯,和他家人一起吃饭,而此时这位曾在叛国罪审判中死里逃生的“煽动者”正在寻找一处退隐之地。这是令人感慨的怀旧与对友情的忠诚。
1813年,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华兹华斯成了国家税收服务的代理。这是一种自我背叛的妥协吗?这个行为给他的名誉带来持久的伤害。1810年代末,拜伦替所有年轻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表达了对华兹华斯的失望,嘲笑他“在朗斯岱尔勋爵的饭桌上”讨好逢迎。吉尔承认拜伦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也为华兹华斯提出辩解:工作是满足诗歌天职和家庭需要的体面途径。(489页)关于华兹华斯的前后变化,他自己对“政治变节”的指责非常敏感,而年轻的激进分子则自认为铁证如山。雪莱夫妻读了华兹华斯的《漫游》感到非常失望。“他是个奴隶。”玛丽·雪莱在日记中写道,雪莱则哀叹他的迷失:“背离这一切,你让我悲哀,/ 既然如此,你不必存在。”但是华兹华斯坚称他的观点、原则都没有改变,吉尔指出假如华兹华斯发表了所有写过的文字,那么他就很难否认他的改变。(531-532页)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政治的险恶风云中,华兹华斯曾经激进的过去还是被人翻了出来。皮科克在他的讽刺小说中对华兹华斯和他的朋友的批评比较难听,但是玛里琳·巴特勒说是“一针见血”:“我们看到一小帮诗人,他们从南方的溪谷带了他们曾奉献给真理和自由的竖琴来到这里,要想在山风里采集新的活力:现在这些竖琴已调了音,适合于颂扬奢华的权力,弹奏宫廷里溜须拍马的调子,赞美已被破除的迷信。”(同前引书,222页) 王佐良教授则认为华兹华斯“曾经同情穷苦人民,曾经为自由而歌,曾经鼓吹爱,但是现在他一步一步接近英国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的立场,一八0九年他写文章指责英国反法战争进行无力,认为需要强有力的超人式的领袖,他甚至主张成立一个特别的骑兵部队来镇压当时已在英国城市里出现的罢工工人。这样,他的政治观点已不止是反对法国雅可宾党人,而是对英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也持死硬的敌对态度。这也是一种从纯真的童年和热情的青年的倒退和僵化,这也是‘幻觉的闪光’的消失,而最后承受这个僵化的损失的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8-89页)
吉尔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际冲突问题的看法很值得思考:华兹华斯对他的自然继承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的影响是复杂的,“他们都承认华兹华斯早期诗歌的自由革新力量,但在有生之年,他们也认为华兹华斯政治变节,因而扼腕叹息。然而,华兹华斯的崛起恰逢他们的早逝,所以,他的声名没有受到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作品的挑战。如今,华兹华斯的早期诗歌在新一代人中获得共鸣,尽管语境相当不同。对于维多利亚早期的成熟作家来说,华兹华斯早年诗歌的政治动荡背景不过是历史云烟,他的政治转变也无关紧要。拜伦、雪莱和济慈都亲眼目睹《抒情歌谣集》的作者成为朗斯岱尔勋爵的密友和保守派的辩护人,但下一代人从《抒情歌谣集》《漫游》和《重游耶罗》中各取所需;他们的前辈对诗人的思想转变感到失望,但他们自己对此并不关心……当年轻的一代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选择自己之所需,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在重新阐释诗人,并非有意或争辩,而只是强调他们看重的价值。”(676页)从英国浪漫主义的代际冲突来看,问题的确并不严重。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浪漫主义的最大迷途和最可怕的变节发生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萨弗兰斯基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中追问为什么浪漫主义确实参与了纳粹法西斯的胜利凯旋。这才是浪漫主义史上最严重的时代悲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