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教条化趋势分流: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下)
【编者的话】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发了一组重要的文章,包括《陈翰笙与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以及两篇译文。《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 中国作者文献选编》一书中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来源于由范世涛译自太平洋国际学会书记处研究员编选、翻译的《农村中国:中国作者文献选编》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
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薛暮桥年谱》项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涛曾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在现代中国经济史、比较制度分析。
陈翰笙领导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始于1929年,终于1933年,在学界享有盛誉,但也歧说纷纭,扑朔迷离。作者综合使用国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以及陈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对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过程、理论准备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报告。
文章提到,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陈翰笙以理论结合实际的经验调查方法回应重大问题,与同期莫斯科趋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形成范式分流,进而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上海。不仅如此,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当事人在参加陈翰笙主持的农村经济研究过程中建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能力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仍在发挥作用。”
原文近25000字,分五个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从莫斯科辩论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主持中研院无锡调查”“从马季亚尔到列宁、考茨基:数据整理过程中的理论准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之建立: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转移”。
我们摘编在此,分享给朋友们,此为报告下篇,上篇详见链接。
找到“无法找到的报告”
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和报告起草过程历时甚久,研究报告也未尽及时发表。当事人回忆调查成果时集中于当时未发表、后来未找到的一份,以致学界普遍误会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只完成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也已经无法找到。事实上,以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完成的报告并非只有一份,过去认为无法找到的报告,借助考证技术,也可以发现主要内容已经披露于英语文献中。为全面认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有必要整理一下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系列成果。
秦柳方、钱俊瑞合写《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本项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调查材料之一部分》、廖凯声《无锡农村调查记略》和韦健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均为理解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必读参考文献。除这三篇文章之外,无锡农村调查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如下五、六种作品:
(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
此文最初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是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0年度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份工作报告中的社会学组部分不久单独成册,并冠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书名。
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看,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间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研究工作并不仅仅聚焦于农村,都市也处于突出的研究位置,甚至一度较农村经济研究更为优先。在调查都市社会时,社会学组“首先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之调查着手”。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社会学组在上海杨树浦区调查全部530家工厂中的474家,实际调查人员42人,调查规模和延续时间并不比1929年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逊色。调查发现,“纱厂丝厂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实为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在中国特有之征象。”从收集的工人家书看,“虽喘息绞汗于工厂机器行间,精神上仍不免乡间亲属之牵累”。目前尚不清楚此次杨树浦调查与上海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但对1925年爆发过五卅运动、1926—1927年曾发生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上海来说,杨树浦调查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引起了“反动派对我们的注意”“要调查我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蔡元培劝陈翰笙改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社会科学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下年度研究计划大纲”部分明确表示,“下年度本组专门从事于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与研究”“本年度杨树浦调查所得材料,则请本所经济学组计划整理”。
因此,陈翰笙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虽然最先开展的实地调查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但主要聚焦于中国农村研究是特殊政治局势下接受蔡元培劝说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研究设计。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原为覆盖城乡的经济调查有机组成部分,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才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首要重点。
为什么社会学组工作报告标题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陈翰笙在报告中说,“构成今日中国社会之经济的事实,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以前之种种关系。吾人所谓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吾人所谓乡村,其性质不似Country。即与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相较,都市之来历非Polis及Compagna Communis 可比;乡村之组织亦非Mir及Manor可比。”这可以看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的纲领性解释和说明。其要点在于并不采用英美农业经济学通行的以农户如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一样行动的经济主体假设,而是在社会经济史跨国比较的宏大纲领之下观察和报告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吸收了马季亚尔对中国政府统计的尖锐批评,也与马季亚尔强调的分区域研究中国农村思想一致,强调农村经济调查“势必分区进行”。不过,报告认为关于划分区域的标准知识“现尚缺乏”“不得已只能先从农村经济显然特殊之地方着手调查”。报告列举了无锡的特殊之处,并就实地调查所发现的复杂度量衡、田权关系加以介绍。
陈翰笙与薛暮桥、冯和法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合编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专门收录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作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置于全书之首,表明此文的纲领性地位。关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指导思想和最初成果,提纲挈领的总体解释和说明均包括在这一论著中。
(二)陈翰笙、王寅生、张辅良、廖凯声、张稼夫、李澄、徐燮均著《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1929)
此书(以下简称《亩的差异》)被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一号”。
《亩的差异》共计7位作者,除陈翰笙和王寅生外,另外5位均为1929年无锡调查后中研院正式聘任的调查员,张辅良还在1930年4月被改聘为助理员。这7位作者显然是1929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初期整理工作的主要人员。
陈翰笙晚年回忆,无锡和保定的调查资料,“由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和我以及其他三人整理”;秦柳方沿用此说,称无锡调查告一段落后,“这些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等7人整理”。上述回忆并不准确。原因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历时甚久,工作人员并不稳定,有人中途退出,有人中途加入,前后参加调查资料整理的人员也就大大超过7人。在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间,《亩的差异》7位作者中的3位(张辅良、廖凯声、李澄)先后去职;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钱俊瑞、张锡昌、薛品轩、瞿明宙、石凯福陆续被聘任为调查员。陈翰笙在论文中还曾引用刘怀溥、刘端生整理的无锡农村经济统计表格,可以确定他们参加了无锡调查资料整理工作。即使不考虑其他人员,仅上述调查资料整理者已有14人之多,比陈翰笙、秦柳方所回忆的资料整理人数整整多出一倍。
除了作者署名,《亩的差异》的主题和内容同样值得讨论。“亩的差异”是马季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第一章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他说“中国农村经济的统计对于各种材料都不正确。关于耕地的面积,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收获量的多少,每亩的面积有多少,这些材料都各自不同。”可以想见,1928年陈翰笙读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征求意见稿时,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而“亩的差异”成为无锡调查的基本内容,也是资料整理首先处理的问题。
《亩的差异》开创性地对22个调查村1204户的农田田块逐块调查,发现无锡所谓的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同一个村亩的差异至少有5种。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由于亩的差异因素,无锡调查资料整理的第一步就是先折合各村户调查表中的亩为统一的度量衡,这必然是繁重的计算工作。
《亩的差异》报告的事实扎实有力,至今仍可以提醒学者严肃对待数字的含义,用陈翰笙的话说,“苟所有地与使用地之实际面积不求真确,则与土地有联带关系之各项农村经济统计,均将全部动摇矣!”
(三)余霖《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1932)
“余霖”是薛暮桥常用笔名之一。该文发表于萧淑宇主编《新创造》第2卷第1、2期合刊“中国农村经济专号”。
薛暮桥原为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主编《民众周报》的编辑员,1932年初应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同学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来信邀请,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参加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4月底,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编制缩小,薛暮桥作为办公费支薪的编外人员被裁减,但仍与王寅生等一起到南京。为维持生活,“陈翰笙教我学写文章”,回家乡无锡礼社镇调查后完成报告,陈翰笙加标题“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后,送《新创造》杂志发表。因此,这是薛暮桥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不支薪的情况下由陈翰笙指导完成的作品。
薛暮桥自述回家乡调查一个月,但陈洪进以含蓄方式谈及此次调查时,称调查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星期”,说薛暮桥“久离家乡,有次偶然重返故里,亲戚好友,都少不得洗尘款待,登门拜访,闲话麻桑,不到一星期的工夫,他已经把这个村庄几年来的变化,弄得清清楚楚,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极详细的文章,把这个中国农村的细胞做了一次标本式的考察,谁也看不出这会是利用一星期的时间有计划的发问,有计划的记录的成绩。”这样看,薛暮桥的调查为时不长,是回乡后有意识发问和记录,然后整理成报告的。这与陈翰笙和王寅生1929年主持实施的无锡农村调查方法明显不同。
薛暮桥礼社调查正值麦熟“即在目前”的青黄不接时间,江南农村的贫困达于极点。据当时报道,无锡桑田掘去十分之七,“这出产丝的地方从此后怕不能再有上丝的出产”“而现在将到割麦的时候,壮丁们都饿得在床上睡,眼看着麦虫吃麦穗;稻田正等着车水,又有谁去做?”而政府仍在催收钱粮,结果出现了无锡抢米风潮。在此背景下,礼社调查记述了镇上地主挟其经济上及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凌驾农民之上的种种情形;认为自足经济迅速破坏,都市工业品长驱直入,家庭手工业首当其冲,都市高利贷资本假手乡村地主侵入农村;“农村经济之恢复,已非空言改良所能奏效也。苟非有绝大之决心,行彻底之转变,决不能挽此厄运也。”报告篇幅不长,但涵盖了人口、宗族、地主、农民、租佃、行政、党部、商团、农会、教育、田赋、税捐、家庭手工业、阶级、革命等宏大主题在江南村庄的实际情况,是一份精要的中国经济史文献,也反映了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者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基本看法,其中关于宗族的格外重视间接体现出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共同的关切。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是薛暮桥完成的第一篇经济学专业作品。文章发表时,张锡昌以笔名“李作周”在同一期《新创造》杂志发表论文《中国底田赋与农民》,其中谈到“无锡西北乡小小的一个礼社镇,三四年来积欠的田赋居然在3000元以上,积欠的原因也是地主‘抗不完粮’”。这显然也来自薛暮桥礼社调查。《江南农村经济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后,冯和法将其收入《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一书,但删除了标题和末尾一段。这篇文章还被日本《改造》杂志译载,薛暮桥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发现时“真是又惊又喜”。
《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吸收了陈翰笙、王寅生等人在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和资料整理时积累的经验,但调查方法更为灵活简便,形成一种薛暮桥称为“农村通讯”的调查报告形式。“过去许多学术机关的调查,往往动员许多人马,抱着一大堆的调查表格跑进农村中去,调查完毕以后,还要带回研究室来,慢慢整理,细细研究。这样的调查纵然可以做得尽善尽美,但在我们乡村工作青年,总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而薛暮桥的礼社调查和写作方法较少限制,便于分散实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年12月正式立案成立后,农村通讯即成为“编辑工作的一个主要的部分”,并在中华书局《新中华》第2卷第1期起设立“农村通讯”栏目,专门发表会员农村通讯作品,薛暮桥的笔名作品正是这一栏目开篇之作。薛暮桥主编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期间(1934—1938),农村通讯是杂志的基本栏目。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将农村通讯的代表性作品单独集合成册出版,不仅希望这些作品成为社会经济学家参考资料,还希望因生动的笔调成为文学艺术研究者的读物。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生于光远谈及,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些农村通讯对自己的“思想进步起过颇为重要的影响”。从于光远的案例看,这些农村通讯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预期。
总之,《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既是薛暮桥中研院期间在陈翰笙直接指导下完成的调查报告,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日后失去中研院这一官方学术机构支持后,以不同于前的分散方式延续实地调查工作提供了新的经验范本,因此在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研究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英文本《农村中国》第2章(1932)和第6章(1933)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馆特藏太平洋国际学会档案,《农村中国》是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1905-1984)1937—1938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完成的研究项目。书中主要收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农村经济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陈翰笙1933年7月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前,主持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所完成的两种未刊报告稿主要内容。第一种未刊报告题为《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Wong Yin-seng,Chien Tsen-jui and others,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2”) ,英译和编辑后列为《农村中国》第2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U,NEAR SHANGHAI”);第二种未刊报告稿题为《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Wong yin-seng,Chang Hsi-chang and others,Modern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3”),英译和编辑后列为《农村中国》第6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最近考证研究表明,的第一作者均为陈翰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3-1951)机关刊物《中国农村》(1934-1943)合订本,薛小和藏书,无锡电视台摄影
《农村中国》中这两章的核心内容最早见于1932年夏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无锡田权正在近代化之过程中:田产买卖,日趋自由;租佃期限,逐渐缩短。因此田权更易集中。无锡农民所有农田,几占全县田亩之半数。地主多不自经营,其所有农田88%俱为出租;农民耕地不足,多向地主零星租入。租地占农田52%。”鉴于两份报告罕见重要的文献价值,对其形成过程有必要做更进一步讨论。
“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按照经济地位将村户分为“地主”(landlord)、“富农”(rich peasant)、“中农”(middle peasant)、“贫农”(poor peasant),另外还谈到“农业工人”(field worker),实际上隐含了“雇农”概念。因此,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个标准的村户分类框架,印证了学界此前指出的陈翰笙主持和实地调查时制订的农户分类标准“发生在1933年以前”“陈翰笙教授的过人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学界之所以将1933年作为评论基准,是因为毛泽东1933年10月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起草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钱俊瑞晚年表示,“在农户分类上,我们用的是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以所处经济地位来划分。他们(指卜凯等人———引者注)却是用自耕农、佃农、半佃农等,以经营形式来划分。这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决定了揭露还是掩盖阶级矛盾的根本问题。”这一回忆忽视了无锡农村经济资料整理的复杂过程,1929年开展无锡农村实地调查时,这一可操作的分类框架尚不存在,但并不能说当时就是“掩盖阶级矛盾的”。只是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这一村户分类框架才明确和确立下来。而这一框架的确立,也标志着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取得长足进展,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派研究范式的成熟。
“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章除了村户分类框架引人注目外,报告还通过土地所有权的类型、移转方式、土地分配、租金运用及土地利用分析,呈现出无锡农村土地集中过程和租佃制度嵌含于广泛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现实。这与马季亚尔所谓帝国主义入侵后亚细亚生产方式残余布满中国的看法相对,既印证陈翰笙关于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肇因于和马季亚尔莫斯科辩论的回忆,也可以看作是精心研究之后对马季亚尔的正面回应。
“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章指出,只是在资本主义形式的财产所有权占主导地位时个人所有者才有权根据意志使用或毁灭财产;在此之前,土地往往由整个家庭或家族所有,且这种所有权残缺不全,其移转受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限制。随后,该章分析了中国农村永佃制正在瓦解,土地财产所有权及其交易变得越来越完整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农村派此后各种农村调查报告的土地产权基本分析框架,因此带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权分析源报告的性质。
(五)陈翰笙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加拿大班夫双年会上的论文(1933)
这篇英文论文共使用31张表格,其中10张表格使用了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数据。其中,无锡土地分配表由刘怀溥、刘端生整理,江苏374个大地主主要职业表由瞿明宙整理,江苏4县当铺表由石凯福整理,直接来自1929年农村调查的数据并不多,这印证了陈翰笙主持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复杂过程的判断。
该文在国际上得到高度评价,“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这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虽然并未在学术期刊刊出,仍在学界引起关注。尤其是这篇论文指出,与大革命前法国旧制度下的地主大为不同,中国的地主常四位一体,同时是收租人、商人、高利贷者和行政官员。这既是一个宏大的分析框架,也指明了中国农村制度与欧洲农村的不同之处,给英语学界留下深刻印象。论文指出,中国的地主并未走上普鲁士的经营地主道路;而“中国的富农也经营高利贷和商业,如同地主一样”;俄国资本主义农业向前发展时,贫农将土地出租,富农租进土地,而长江流域,贫农多是佃农,富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这也就表明了世界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类型在中国前途黯淡,中国的地主和富农致力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持续,贫农、雇农和中农失去土地,地主和富农集中土地,并不是为了改善生产而是使既有的生产方法加强。这篇论文引用马季亚尔的地方不多,考茨基和列宁的名字均未提及,但关于土地财产长时段变化的讨论受到马季亚尔的深刻影响,收租人、商人、高利贷者和行政官员四位一体的看法在马季亚尔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至于经营地主和富农的讨论则反映了考茨基和列宁著作的影响。
这篇论文完成于1933年5月,此时陈翰笙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8月在班夫会议上正式报告时,他实际上已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改任社会科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因此,这篇论文实际上是陈翰笙任职国立中央研究院期间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是他领导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的系统总结,当然也包括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的总结。至此,一个肇因于1928年莫斯科辩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范式,已经以成熟的方式展示给国际学术界。
“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
虽然索讷指出,1880至1930年间俄国农民经济研究最领先、记录最完整,薛暮桥指出在莫斯科工作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部完整著作”,莫斯科在农村经济(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面一度表现的开创性并未延续下去。这可以用陈翰笙1927—1928年客座访问国际农村研究所时的经历解释。他晚年回忆: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
陈翰笙1927—1928年在莫斯科所观察到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年愈演愈烈。马季亚尔的著作在苏联引起巨大的争论,1930年和1931年曾专门召开两次研讨会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与会者只是引经据典援引有利于自己看法的语录,对经济事实并未进行切实的深入研讨。陈翰笙带领的研究团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在同一时期深入无锡农村,以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加以回应,与莫斯科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内部的研究范式分流。
这种范式分流结果是莫斯科失去了农村经济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传统的领先地位,而陈翰笙主持的研究则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前沿。除了苏联方面,英语文献也高度评价陈翰笙的研究工作。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长篇论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陈翰笙本人在评论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农村经济研究时,坦率地指出俄语研究文献在提供数据方面“毫无意义”。这是对苏联1930年代农民和农村经济经验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衰落的权威评论,也是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教条化的一个侧面。
陈翰笙1935年再次访问莫斯科。他回忆这次访问“给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俄共(布)清党的紧张气氛”“我所认识的一些苏联研究员,有的莫名奇妙地失踪了,有的开枪自杀了。到后来,加拉罕和马季亚尔也受到审查、被处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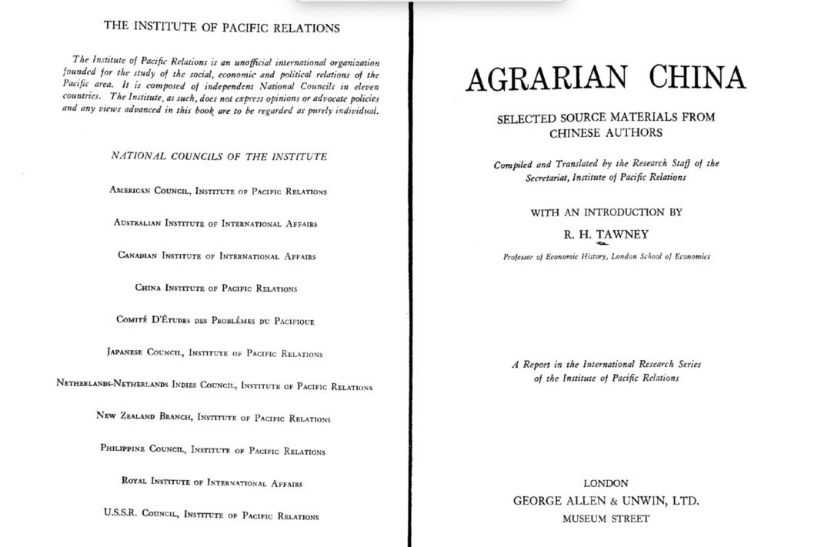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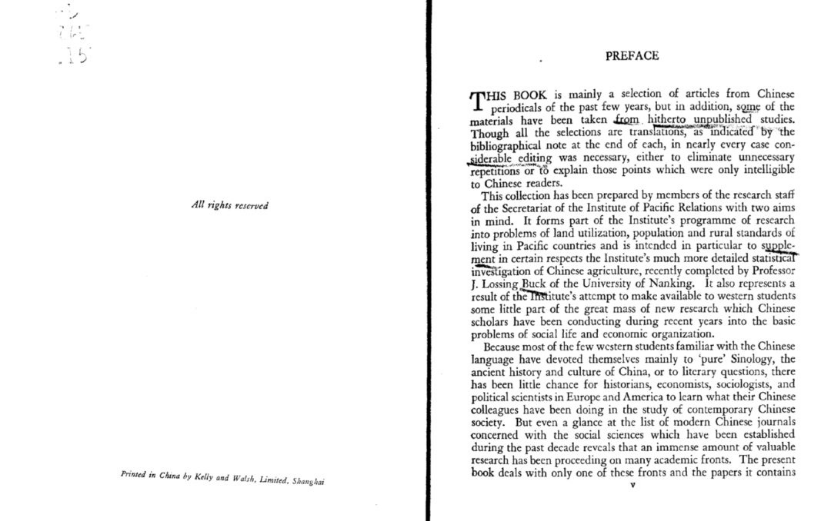
《农村中国》,内页划痕为费正清笔记。感谢作者提供图片
原文及《无锡的土地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前途》 《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见链接。
